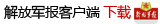说人心
先入函谷关的刘邦,为何与民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败走新野的刘备,为何不弃百姓、携民渡江?就是因为他们识得人心的力量。
春秋时期,郑国任命子产为相。子产上任后,秉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心态,相继实施了包括整顿田制、作丘赋、铸刑书等一系列改革。然而,老百姓接受这些,并没那么顺畅。
子产从政一年的时候,百姓评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从政三年后,百姓称颂:“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从“谁要杀子产,我助他一臂之力”,到“子产死后,谁能继承他呢”,这里的变化,就是人心之变。
人心是个千古命题。什么是人心?明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道:“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由此可知,人心是一种判别和选择、权衡和朝向。正因此,顾炎武把人心视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老话说“人巧胜于天”,这里的“巧”就是人心的不同。谢肇淛曾有一番对比说明:“一尺之面,亿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亿兆异向,此人之巧也。然面貌,父子、兄弟有相肖者矣,至于心,虽骨肉衽席,其志不同行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人与人之间经历不同、诉求不同、认识不同,人心自然不会完全一样。
《文海披沙》中,有一段论及古今人心不同。里面说:“俭,美德也,古以养廉,而今徒以守货;隐,高风也,古以避世,而今反以吊名;狂,奇节也,古以进取,而今借以肆詈;勤,盛心也,古以修业,而今用以治生;学,本业也,古以成材,而今专以取贵;戒杀好生,善事也,古以自尽其方寸,而今以徼福于幽冥。”随着时代和环境变迁,人们对一种美德的坚守,内涵也在发生变化。
人心与世风密切相关,世风淳朴则人心素洁。清代纪晓岚笔下,有一则故事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道理。德眘斋扶乩请神,大仙降临后署名“刘仲甫”,此人是宋代独霸棋坛、所向披靡的大国手。旁观扶乩的人群中,有知晓刘仲甫的围棋高手,便邀其对弈。刘仲甫说:“下棋我必输。”大家多番请求,刘仲甫终于同意。行棋走子,刘仲甫果然输了半子。
刘仲甫的落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家认为,这是大仙谦让,鼓励后进。刘仲甫予以否认,他说:“盖风气日薄,人情日巧,其倾轧攻取之术,两机激薄,变幻万端,吊诡出奇,不留余地。古人不肯为之事,往往肯为;古人不敢冒之险,往往敢冒;古人不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故一切世事心计,皆出古人上。”借对弈言对心,纪晓岚的用意,大抵是兴教化、纯世风以净人心。
人心有异同、有寒暖、有移固、有向背,若导之有方、教之得法,向善向上的势头就强劲。古人说“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这个“心”指的是圣贤之心,它是一种健康积极、能量充沛的价值观。缺乏这种价值导向,世风人心就会停留在微笑曲线的底端。
“复礼,复心也;行事,行心也。”人心之力,不可估量。它就像风一样,当呈现“微”的状态,一纸之隔都难以穿透。“及其怒也,拔木折屋,掀海摇山,天地为之震动,日月为之蔽亏”,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先入函谷关的刘邦,为何与民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败走新野的刘备,为何不弃百姓、携民渡江?就是因为他们识得人心的力量。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西周之时,召公治理陕以西之地,就特别注重教化民心、敬顺民意。他巡行乡邑,听断于陇亩之间,庐于棠树之下。“召公卒,人思其政,怀棠树下不忍伐,作甘棠之诗歌咏之。”甘棠遗爱的大美诗篇流传数千年,它实在是对“人心”最清亮的注解、最美好的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