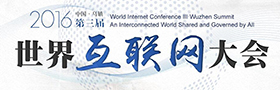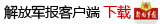李斯之“私”在他嫉贤妒能谋害同窗上尽显无疑。李斯与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有同窗之谊。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先天严重口吃,但嘴笨思深,善于著书。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看了《孤愤》《五蠹》等书,非常感慨,说:“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并与他交往,即使是死了也不遗憾了。”因此,加紧攻打韩国。危急中,韩王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高兴,预把韩非留在秦国任用。李斯妒忌韩非,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诸侯,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效力,而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久留于秦,将来再放他回去,这是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以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有道理,派人将韩非关押起来。趁此,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要向秦王申诉,但未能见到秦王。秦王后来悔悟了,使人去赦免韩非,但韩非已经被害死了。李斯非常了解韩非的才能,当看到秦王欣赏并准备任用韩非时,在秦国政坛立足未稳的李斯,把韩非看成是自己飞黄腾达的绊脚石,无情地把同窗毒死在大牢。
李斯之“私”在“焚书坑儒”事件中可见端倪。“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儒士淳于越认为周青臣等人在面谀始皇,有不忠之嫌,起而进谏:“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为自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弟子为匹夫,卒有田长、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本来是臣子之间的政见之争,也是正常的国事进谏,但李斯却借题发挥,推波助澜,酿造了惨重蠧害中华文化的“焚书坑儒”事件。李斯深知,秦始皇绝不苟同“分封诸侯”。在实行“诸侯制”还是实行“郡县制”这个根本问题上,秦始皇与被罢免赐死的丞相吕不韦早就有过重大分歧。李斯对秦始皇的主张心知肚明,已经揣摩透了秦始皇的心思,给秦始皇上书,把儒士们的看法和议论说成是非议当世、惑乱民众、崇古害今、非主博名、率群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当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益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穷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这样的上书,完全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顺应了秦始皇的心思,秦始皇自然很乐意采纳,批准“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由此,又诱发了“焚书坑儒”事件,也终结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局面。从中也不难看出,李斯谀上私己的真实用心。
李斯之“私”在处置君臣关系中昭然若揭。秦灭六国后,集中了十余万六国罪犯大修骊山陵,人称十万刑徒,时有作乱,工地深藏着骚乱动荡的危机。这时,秦始皇让李斯征发老秦人去骊山修陵,李斯这时才给秦始皇算了两笔账。一是详尽列出了老秦人被征发南下、东进、戍边、迁徙及伤亡的数量,指出关中腹地所剩老秦人尽是老弱妇幼,已无人可征。二是如果再从被灭六国的青壮年中征发,骊山则将聚集六国的数十万精壮人口,若趁机生乱,则是肘腋之患。这两笔帐道出了事关大秦江山稳定的严峻危机。老秦人是大秦王朝的命脉,是大秦江山的根基,在六国复辟暗潮涌动、大秦一统江山未稳之时,关中一旦有变,天下一旦有变,老秦人再没有可成军之人,关中也再没有老秦兵可用,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两笔账让秦始皇大为震惊,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此重大的隐患,李斯又如此的清楚,为何不早说出来?为何不及早指出这个如此重大的失误?这就是李斯的权利机谋。他时时处处留心,刻意周全,二十多年中与秦始皇从没有任何歧见,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老臣中所有人都与秦始皇发生过政见争执,唯独李斯没有,契合得如同一个人,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正如王贲临终遗言:“丞相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就连他早以了然于心的重大隐患也不及时进言,而是揣摩君心、察观权机,刻意选择进言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