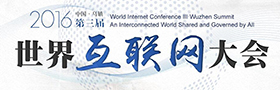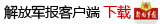为官要去“私”
——惕厉李斯的悲剧人生

读罢《大秦帝国》这部6卷11册500余万字亦史亦文的长篇巨著,战国云烟滚滚而来,大秦雄风浩浩而至,内心波澜汤汤而起。禁不住,再次捧起《史记》这部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篇巨制,乘着中华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去探寻那些撬动了乾坤的历史巨人的足迹,领悟透析他们人性的光辉与晦暗、人格的高尚与卑微。两部煌煌大作,一脉华夏风云。掩卷长思,无不被“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精神魂魄所深深震撼,被秦嬴政“扫六合,统天下”的雄才大略所深深折服,更为辅佐秦嬴政、为大秦帝国立下不朽之功的“千古一相”李斯的悲剧人生所扼腕浩叹。
李斯洞悉天下大势,独具雄阔眼光,以超人的才识为秦王和秦国提出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大争目标;献离间计,瓦解六国君臣关系,动摇六国政治军事基础;上《谏逐客书》,保护了自己,也为秦国留住了大批人才;呕心沥血,精勤侍业,多次化解重大危机;殚精竭虑,盘整华夏,创制帝国集权框架;力排众议,推行郡县制,巩固集权统一;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书、度量衡;辞藻文章先秦无人可比,如鲁迅所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李斯文才可经世、治才能定国,堪称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不愧“千古一相”。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所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推翻了一个世界。”然而,正是这个能使天崩地坼、推翻了一个世界的“千古一相”,却沦为阶下囚,受到“黥刑、劓刑、断舌、砍趾、腰斩”五种酷刑,并被夷灭三族。
李斯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人生结局,是学识不足吗?是才具不够吗?是智慧匮乏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要拉直这些问号,需要在李斯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中寻求答案。
《史记·李斯传》开篇写道:“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的“老鼠哲学”。李斯认为,同是老鼠却有天壤之别。厕鼠,食厕中不洁之物,还得担惊受怕;仓鼠,食大庑之粮,却无扰无惊,关键是它们的处境不同。人有没有出息、富贵还是卑贱,无异于厕鼠与仓鼠,全在于所处的环境。于是,他不甘心做厕鼠,辞去低下的职位,去跟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期求进身帝王之侧,改变人生命运。
李斯学成后,向老师辞行时说:“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他认为,处在卑贱的地位而不想方设法去改变,就像只会吃草的麋鹿看着肥肉而不能吃,空有一张人的面孔勉强能行走罢了。所以,耻辱没有比身份卑贱更大的,悲哀没有比处境穷困更甚的。长久处在卑贱的地位、穷困的环境,却愤世嫉俗、厌恶名利,自安于无为无求,这不是士人的情怀。他还认为,“得时无怠”,在看准了秦国强盛、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的时机,选择西去侍秦,而不是去为自己的楚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