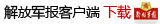二
李熙玉:您的研究引发了有关中国模式的很多讨论。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到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以及是否可以普遍适用等等,学者们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在韩国,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也一直在进行当中。不知您对中国模式持何种见解?
张维为:我想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思路和制度安排。无疑,中国今天的巨大成功,背后是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国际竞争中形成的,所以我认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的开放,中国愿意汲取别人的一切长处,但绝不失去自我。这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模式,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模式。
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模式,西方认为它那个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到处推动“颜色革命”,但看一看乌克兰“颜色革命”带来的内战,看一看“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看一看西方自己也陷入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西方模式怎么可能是普遍适用的?
中国模式当然也不是普遍适用的,但一个模式真的成功了,别人会来向你学习。今天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从俄罗斯到中亚国家到印度到越南,都在借鉴中国的经验,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非洲和拉美。但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到处推销自己的模式。所谓普遍适用的模式,基本上是西方一神教思维的产物。福山先生的“历史终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也根本站不住脚。关于这一点,我在上海和福山先生辩论过,我的观点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之道,它可以借鉴其他模式中的有益成分,但照搬别人的模式必然失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模式,像其他模式一样,有自己的问题和缺陷,但它能够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它纠正问题的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得多。
李熙玉:对于“中国性”(chineseness)的讨论,西方多数人持否定评价,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从研究角度来看很难把它科学化。正是因为对于究竟哪些东西可以称为“中国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模糊不清,才存在或引发了各种误会。不知可用何种方式对“中国性(中国的)”进行评价?
张维为:否定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的学者,大都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特别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的影响。我对这一类政治学理论的评价很低,其重要原因是基于这种学理对中国所做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与其说是科学化,不如说是伪科学化。
研究政治的人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了解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自己的传统形成有数千年,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才数百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好朝代持续的时间比整个美国历史都长,用西方几百年的经验来诠释有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中国,确实很难。这就是我从西方政治学者老是误判中国后得出的简单结论。
我和我的同事正在进行解构西方话语的工作,破除对西方社会科学所谓“科学性”的迷思,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性”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自己的特性,这是一个常识判断,学术上也可以说得清清楚楚,不会引起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