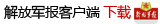会说话者不啰嗦
语不费饰,清味自悠。
相传欧阳修担任翰林时,曾与同事出游,在街上遇到一匹奔马踏死了一条狗。欧阳修提议大家用简洁的话来叙述此事。一人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一人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说:如果让你们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他仅用了6个字,就把事情说明白了:“逸马杀犬于道。”字数却比前两人少了一半。
俗语说,“好话啰嗦三遍,鸡狗都不稀见”。可见人们对于说话啰嗦是多么厌烦。古时有位“啰嗦先生”进京赶考,写信给妻子道:“吾妻如见:前日啰嗦今日不复啰嗦矣!吾在下月即将返里,不在初一即在初二,不在初二即在初三,……不在二十八即在二十九,所以不写三十,因月小之故也。家中有棉鞋一双,望吾妻取出来拍打拍打,所以要拍打,因灰尘之多也。希吾妻千万不要忘记。为省笔墨起见,吾不写草头大万,即以方字去点代之……”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把啰嗦人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短话长说,往往是由于铺陈罗列、言之无物的内容挤占了空间。对于这类繁冗的语言,有人比作“懒婆娘的裹脚”,有人讥为“婆子舌头语”。正因为说话啰嗦,有人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明朝朱元璋当皇帝时,刑部侍郎茹太素上疏,“论时务累万余言”,朱令人读到6千多字时,还未听到半点具体意见,龙颜大怒,叫人把茹太素打了一顿。次日再往下读,读到1万多字后,才知道他建议办5件事。朱元璋指出,这5件事几百字就可说清,根本不必如此啰嗦。
还有些人,明明不善说话,却又生怕人家以为自己不善说话,于是故作姿态,甚至东施效颦。
隋代侯白的《启颜录》中记载,梁代有个痴人,不知道帽子为何物,偏要儿子买一顶来给他戴。他对儿子说:“吾闻帽拟成头,汝为吾买帽,必须容得头者。”结果儿子买了一个能“容头”的瓮子回来。他戴上这个“瓮帽”,“没面至顶,不复见物”“研其鼻痛,拥其气闷”“鼻上生疮,项上成胝”,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不肯脱掉“帽子”。今天,那些说起话来“穿靴戴帽”者,看到此笑话该作何感想?
其实,说话该短不短,恰恰是没水平的表现,会说话的人从来不说啰嗦话。要使语言精炼,必须花点工夫,向会说话的人学习,看看人家是怎样长话短说的。比如,唐代韩愈是“惟陈言之务去”,宋代陆游是“句中无余字,篇外无长语”,鲁迅先生是“可省之处,决不硬添”,莎士比亚则是“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
以精炼有力的文字镂神辟幽,揭示事物的本质、烛照事物的意义,殊非易事。因此,遣词造句学会“掐尖”,挑选素材、事例、引文,就要挑那些新鲜、独家、绝门的;啰嗦的话“格杀勿论”,“车轱辘话”该删则删,冗言冗语或舍弃、或概括。如此,文字自然就能短下来。
动人心者不在言多。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内部妥协气氛弥漫。其时,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发了一个“电报提案”。全文不过110字,第一部分最终浓缩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个字,该提案被爱国人士邹韬奋称赞为“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文章贵约,但也不是短的就一定比长的好。文章为时而著,是长是短要看实际需要。实事求是、言之有物,是一个根本原则。总之,应当坚持“篇幅服从效果”这一原则,能用三言两语说清绝不拖泥带水,能直截了当讲明绝不绕弯子,有一说一,务求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