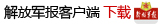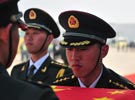《马关条约》谈判和签署地点日本春帆楼(资料图)
遗恨绵绵:中日国运自此改变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打破了清政府“天朝大国”的迷梦,也改变了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态度,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瓜分利益的狂潮。
首先,中日实力易位,日本对华开始由仰视变为俯视。日本人崇拜强权实力的民族特性,使其只敬畏强者,而对弱者缺乏怜悯。汉唐时期,国力孱弱的日本一直仰慕中华文明,主动派使前来交往。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战役中大败于唐军后,更让日本清楚地看到自身的落后,开始全面向中国学习。其后的一千多年间,日本又数次败于中国之手,使其不得不收敛起扩张的爪牙。即便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仍存敬畏之心。1891年北洋舰队定远、镇远等6艘战舰受邀访日,就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震动与赞叹。然而,随着几年后《马关条约》的签署,中日地位彻底反转。日本国力日盛,清政府一蹶不振,日本人对华的敬畏迅速转变为凌驾于人的傲慢。这种狂妄自大的心态,刺激着日本吞并中国及称霸东亚的野心不断膨胀。
其次,《马关条约》的签署,使本已如风中残烛般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更加难以为继。原本,清政府在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推动下大力开展的洋务运动,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国工业、国防体系已初具规模,为发展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甲午战败,使轰轰烈烈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付水东流。《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更是彻底打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日本索取的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8000万两的3倍、甲午战前所借外债总额的5倍多。
为偿还赔款,清政府只得“拆东墙补西墙”,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在甲午战争后的3年多时间里,清政府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3亿两,连本带利共6亿多两。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带政治条件。彼时中国每年海关税收约2000余万两,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其中的十分之七都要用于偿还外债。西方列强凭借庞大债务在攫取利益的同时,也从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中国,中国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民众苦难更加深重。对此,谭嗣同悲愤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再次,日本虽走上富国强军道路,但同时也埋下穷兵黩武、亡国覆灭的种子。《马关条约》中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使日本陡然成为腰包鼓胀的暴发户。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又惊又喜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国库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个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中国赔款使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以迅速完成,大大加速了日本的工业化步伐。甲午战后,日本的财政规模急剧扩大。1894年,日本财政支出仅为8000多万日元,到1899年达到3.9亿日元,5年间猛增5倍。日本一举成为亚洲强国,并由一个被压迫国家摇身一变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中。
同时,依靠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日本军备得到迅速扩充。据日本学者统计,日本所获战争赔款中,5700万日元用于陆军扩充费,1.39亿日元用于海军扩充费,7900万日元为临时军费,另用于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共3.05亿日元,占赔偿金总额的87%。余下经费用于兴办实业,扶植教育等,以进一步强化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马关条约》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日本更加沉迷于军国主义道路和对外扩张侵略。自此至二战结束时的50年间,日本不断挑起对外战争。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日本通过一次次对外扩张掠夺,以战养战,不断透支国力,穷兵黩武,最终吞下了自酿的苦果,在二战后沦为麦克阿瑟口中的“四等国”。
最后,《马关条约》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软弱可欺,西方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日”的名义下,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强租旅顺、大连,不仅把辽东半岛据为己有,更将东北全境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借口山东传教士被杀,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建造胶济铁路,将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则逼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云南和两广变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不甘落人后,除强占威海卫、九龙半岛和大鹏、深圳两湾为“租借”地外,又划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