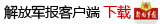那天好大的风,母亲却抄起竹竿,去山里打树上的桂花。她关节不好,可她为我打槐花时,却利索极了。
槐花满满打了一提篮,母亲便载着槐香回来了。一进门,风也猛灌进来。看到母亲兴冲冲地,一大菜篮槐花,晃着,晃着,就这样晃进了记忆里。

我摸了把篮子里的槐花,很凉。又赶紧摸摸母亲的手,也冰得惊人。
却见母亲边抱怨着风吹走了提篮里的槐花,边将槐花浸在冷水里。她怕热水泡坏槐花,始终选择用凉水来泡。母亲的手臂肿胀微黄,在水里洗槐花时却灵活极了。我就看着母亲笑吟吟地将槐花在水里轻揉,那一点点涟漪泛起,煞是好看。
还记得,她从面缸里挖半瓢玉米面的身影。撒点盐,搅拌成面糊时,母亲总要挑一点尝尝咸淡。
那是盐的味道。还带着山的味道,风的味道。
蒸槐花饭的味道又仿佛荡漾在舌尖。蒸一锅,拌上点酱油醋,最后来点芝麻香油,入口之后,清香经久而爽口。玉米面的糯软和槐花的清幽,流泻出均匀的韵律。滋味,竟浓得一时化不开。牙床上,这股清香一遍遍丰满着、涤荡着......
突然感慨口齿噙香这个词是多么高明的创造。也许没有比这个词更可爱、更深入雅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