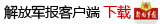甘巴拉阵地全貌。郭超英 摄(资料图)
2014年酷夏,我夜宿阵地第7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20周年。我在阵地上见到了当年第一批登上甘巴拉的战士夏仲昌,听这位67岁的老兵激情澎湃地讲述了甘巴拉人有史以来第一夜。
像熟悉自己的掌上纹络,老兵清晰记得那是1967年8月12日。他和战友们乘卡车抵达山顶时,浓云缭绕、寒风瑟瑟,除了漫山乱石和简单挖过的地基,一无所有、寸草不生……
“架设雷达!尽快担负战备值班!”
只有一个念头,官兵迅速清理乱石,架设装备。山顶狂风肆虐,得用三角钢钎固定防风绳,而坚硬如铁的冻土层,大榔头砸下去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子。高原反应袭来,年轻力壮的小伙儿砸三五下就头疼脑涨、浑身无力。大家便排队轮番上阵,硬是将钢钎一寸寸打进千年冻土,也迎来了5374米海拔的第一夜。
这是亘古无人住宿的生命禁地啊!
天当房地当床,狂风云雾当幔帐。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氧气更加稀薄,官兵露天蜷缩在睡袋中,又累又困,可刚要入眠便因缺氧憋醒,再迷糊又憋醒……
辗转难入眠,起坐待天明。天边刚透出一丝黛青,官兵们便提着工具冲上阵地。雷达天线在雪域之巅屹立起来,雷达电波穿透云雾连续上传,官兵嘴唇黑紫渗血,双眸血丝交错,如暗夜熹微初露,如天际霞光初现……
“最高的眼睛”,从此时刻巡视雪域碧空,担负起对空警戒侦察和军民航飞机引导的重任。
掐指算算,我夜宿甘巴拉,距那时已过去40载。时光移转,条件变迁,官兵住上阳光房,雷达戴上防风罩,氧气设施上阵地,但空气中氧因子依然悭吝,因而,甘巴拉的夜依然难熬。
“自然条件无法改变,我们总不能一天到晚干什么都背着氧气吧?”那夜,耳畔回荡着甘巴拉老兵轻松的反诘,看着制氧机立在我床边魅惑地冷笑,我拼命忍着不吸。
夜更深。我躺下身想快睡会儿,刚要入眠,便被憋醒,索性披着大衣靠在床头……平生第一次觉得表针慢过蜗牛爬行,脑海里浮现出将生命留在甘巴拉阵地的贵州遵义兵许正兵。
入伍后第一次上阵地,他高原反应强烈住进医院,出院后,连队干部要他留在山下休整点,他坚定地说:“我是雷达操纵员,不上山,操纵什么呀?”
再次上山,他高原反应依然强烈,头疼呕吐,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值班干部要他跟水车下山,他双手抓住床沿不放:“老兵说上阵地人人都得过这一关,扛过去就没事了!”
谁料想,这个喜欢弹吉他的兵躺下后,就再也没能爬起来。高原肺水肿,将他的年龄永远定格在18岁,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89年1月13日的雪夜。
夜宿阵地第3年,我又上阵地采访。雷达站第22任站长孔维同担负阵地总值班。这名云南汉子双目炯炯却血丝交错。原来,他感冒刚好,喘气不顺,夜里只能把枕头垫高,靠着打个盹。交谈间,他讲起我夜宿阵地前一年阳春的一个狂风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