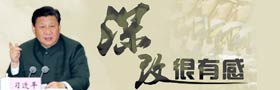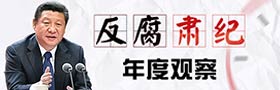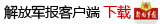写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文/周云峰

在皖南事变75周年到来之际,我记忆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你的样子——一位我军早期高级政工领导的形象:儒雅的身姿,亲切的笑容,圆圆的黑框眼镜背后,是弹线般喷射而出的目光。
那是1941年1月,在安徽泾县的崇山峻岭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中遭受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兵包围,你与叶挺、项英一同指挥部队奋起抵抗,血战七昼夜。14日晚,在突围中,你身先士卒,身中四弹,重伤难行。军部卫生连的战士不肯把你丢下,用树枝扎了副担架抬着你走。
15日凌晨在章家渡渡河时,遭敌阻击,好几个战士中弹倒在河里。你身体极度虚弱,为了战士们能够减少伤亡、轻装突围,你悄悄摸出别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牺牲时,你年仅35岁,用生命践行了自己在生前的战斗动员:“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

青山呜咽,江水悲泣,这壮烈的画面感动了许多人,也深深烙进我的脑海。作为血管里流淌着铁的新四军红色基因的南京军区部队的一员,作为同样从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工作者,每念及此,我总是心潮澎湃、思绪难平,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那时,我就有个夙愿,要到泾县云岭你谱写生命最辉煌悲壮诗赋的地方,走近你、读懂你、缅怀你、祭奠你。
我数次走进云岭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在全面详实了解那段悲壮历史的过程中,在追忆新四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写就的壮烈传奇中,我对你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更为深切的感悟。

当站在你曾经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讲台时,当翻看你亲手创办、精心哺育的《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时;当聆听你主持创作的《新四军军歌》“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时;当抚摸陪伴你度过人生最后三年时光的桌椅枯灯和绿色军毯时;当吟诵你真情创作的《别了,三年的皖南》中“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的诗句时;当领略你在家信中饱蘸激情写的“此刻,我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时……
我的心灵被历史的重锤深沉地撞击着,我眼前的你不再是文献名录中那些冰冷的文字,不再是别人口中那虚幻的影像,你实实在在、有血有肉地矗立于我的面前:你是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一位30来岁多才多艺的青年才俊,你也是一位至情至性、重情重义的热血男儿,你还是一位心中时刻澎湃着不可撼动的信念定力的政工领导,你更是一位关爱战士并能为之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充满血性担当的优秀将领。

在新四军军部大会堂的两侧,留着以前祠堂主人铭刻的“忠、孝、节、义”四个大字,其实就是对你、也是对无数革命先烈为国家民族洒尽最后一滴热血最深刻的写照与注释:忠是将士对人民的忠——忠勇可嘉;孝是赤子对国家的孝——孝感动天;节是正气凛然的革命气节——高风亮节;义是追求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大义——义薄云天。
岁末年初,我和战友们再次来到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凭吊,耳畔又响起你曾经慷慨激昂的诗赋:“十载辛酸斗兵戎,愧我吴下旧阿蒙。半壁江山沉血海,满地干戈斗沙虫。北伐长征人犹在,千伤万死鬼亦雄。弹丸挣扎鱼龙变,地覆天翻见大同。”
我在心里采撷一朵景仰的小花,默默献给你,献给血染皖南那片绿水青山的革命志士、民族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