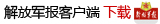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我生命的起点就开始缺席。自打记事起,我就知道,我讨厌我的父亲。我百无聊赖地走进书房,鬼使神差地拉开抽屉,突然瞥见一封信。那是一封父亲写给我而未发出的信!一阵好奇涌上心头,这个老顽固怎么会写信给我?他能在信里写些什么呢?没想到,就是这次“偷窥”,让我终于读懂了父亲。
请关注今日《解放军报》的报道——

对不起父亲,我偷看了您的信
■刘雪玥 口述 栗森阳 整理
“我们这个家族没有太大的荣耀,只有为国家尽点力的愿望。由此,我想和你,我亲爱的女儿一起,把各自宝贵的年华付给戍边事业,也算尽了责任……”
那年寒假回家的第二天清晨,我拒绝了父亲要带我出操的命令,心想,安排我20年了,还不够么?好不容易放个假,什么时候起床我自己做主!可在部队养成的生物钟,早已让我睡意全无,起身想到窗边看看一年未见的风景。然而,拉开窗帘,6点半的乌鲁木齐天空尚是一片漆黑。
我百无聊赖地走进书房,鬼使神差地拉开抽屉,突然瞥见一封信。那是一封父亲写给我而未发出的信!一阵好奇涌上心头,这个老顽固怎么会写信给我?他能在信里写些什么呢?没想到,就是这次“偷窥”,让我终于读懂了父亲。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我生命的起点就开始缺席。自打记事起,我就知道,我讨厌我的父亲。
逢年过节,小伙伴们都要去逛商场买新衣服,到游乐场开碰碰车,可我却被母亲牵着,一路颠簸到伊犁的军营里看父亲。没有旋转木马,还要挤上慢悠悠的老牛车;没有棉花糖,只有戈壁滩上刀割一样的风和沙。我想看动画片,可是有线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电视上满屏的“雪花”;我想和小朋友做游戏,可是这里没有同龄人,父亲带我去听班务会,听战士们聊天说话。
“不待了!不待了!”我大吵大闹着要回家,可母亲却说:“爸爸在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家。”我大声喊着:“不对!我的家在乌鲁木齐!”那一刻,这个被兵抛起来时笑得自在又张狂的男人,难过又无助。
父亲从服务社一袋一袋地给我买回零食,变着法儿讨我开心。他说要给我扎最漂亮的羊角辫,可是擦枪越障的手掌力大得出奇,弄得我生疼不说,好半天折腾也只剩下一头的凌乱和我的哭哭啼啼。我每天都气鼓鼓地闹着要走,跨越千里的团聚对我却是煎熬。分别时,母亲眼里噙着泪,我却开心地喊着“回家咯”,阴沉的天色包裹着母亲强忍的难堪。
上小学时的一次寒假,母亲照例收拾行李,要带我去军营过年。我一直捣着乱,把刚刚在箱子里放好的衣服抖了一床:“我不想去看爸爸。”母亲见哄我没用,伤心地说:“难道要爸爸一个人过年么?”我张口就说:“让他和他的兵过去!”那是母亲唯一一次打我。
或许因缺失的陪伴,幼年时父亲对我还尚且温情,可当我逐渐长大,对人生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并付诸行动终要收获之时,等来的却是他专横粗暴的干涉。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那个从来缺席家长会的父亲,却像一阵风一样冲回了家。他什么都没有问我,就在报名表上独独填写了一所军校。我很认真地说:“我比一本线高了100多分,我可以有很多选择。”他不由我争辩,只下命令:“我们只填这一个。”我怒不可遏:“当兵是你的愿望,不是我的!”“可你是军人的女儿!”那一整个暑假,我与父亲都在打冷战。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我们一家在校门口分别。军校大门外的哨兵抬起手拦住他们俩的那一刻,母亲一下子哭了,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的眼里竟也有泪水在打转。那一瞬间,我从一团模糊中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着急忙慌地跑到服务社给我买零食、只为了哄我开心的男人。一个从军近三十载的老兵竟然在一年的红牌哨兵面前显得脆弱又无助,父亲的确是老了。只是我的心里还填满了无奈和错愕,你让我来的啊,你哭什么?
军旅四年,日出晨练星起守哨,我多少有些体会到父亲对军营的感情,可是横亘在父女之间十几年的沟壑怎能轻易填平?
于是,我看到了这封信。皱皱巴巴的纸张不似父亲的利落干净,满篇都是洇湿的痕迹。他这样写道:“或许多年后你依旧会埋怨我,也或许会因为懂得了责任而感谢我,但我们都知道,既然迈出了生活的步子,就不得不跟着向前走……如今,你正在一天天懂得军装和荣誉的意义,正合了边塞上那一抹绿意。正是这些青春的轮回,才能使得这岁月更具安详醇香的味道。账就是这么算的,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去算,这才能构成一个大国防。我们这个家族没有太大的荣耀,只有为国家尽点力的愿望。由此,我想和你,我亲爱的女儿一起,把各自宝贵的年华付给戍边事业,也算尽了责任……”
读罢,我早已泪流满面。我知道,自己与父亲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拿起笔,接着父亲的话写:“作为一个军人的女儿,作为一名军人,我始终觉得大步走的时候,身后追着的是你的影子。钢枪的重量,军装的含义,笔落之时,重如千钧。爸爸,对不起,我偷看了您的信。爸爸,对不起,女儿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