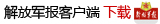我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在属于儿童的节日里,身在军营的我们更多地把铁血柔情寄予可爱的孩童,更多地想起那些远远近近的军娃们。说起祖国的花朵,就仿佛嗅到了芬芳,看到了收获;想到美好的希望,肩头就多了沉甸甸的责任,心中油然升起深情的祝福。请关注今日出版的《解放军报》的文章——

军爸军妈的陪伴,是送给军娃最好的“六一”礼物。 廖 键摄
那座大院,那帮军娃……
■勾敬铭
前几天,受战友委托带他5岁的儿子乐乐到部队幼儿园参加军旅诗词吟咏比赛。当听到一个孩子抑扬顿挫地朗诵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时,不知为何,我竟然眼眶不觉潮湿了起来,思绪随之飞回到20多年前我那色彩斑斓的大院童年。
在军娃们的意识里,家,不单单是三口人的小家,更是百十来号人的大家
那时,我的爸爸是武警河南总队的一名军人。我家就住在总队大院里的一栋筒子楼里。
住在我家楼上的赵鹏,和我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兄弟。他下来找我玩之前,总会在自己家地板上蹦上几蹦、跺上几脚,我在楼下立马就能接收到“信号”。有一次,他来找我,正赶上我在吃妈妈给我煮的方便面。那个牌子的方便面有一袋香油调料,能让普通的泡面色香味俱全,在20世纪90年代也算稀有食品了。赵鹏被惹得馋虫直冒,在我碗边儿转着圈地闻味儿。妈妈见状,二话不说把面从我眼前端走递给了赵鹏。赵鹏端起碗,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就为这事儿,我们友谊的小船差点翻了。
一个大院里住着,真的就是一家人。每到傍晚时分,各家在楼道里支起煤气灶烧饭。你家的胡萝卜炒肉、我家的酸辣土豆丝、他家的麻婆豆腐……整个楼道里烟雾缭绕,各种饭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正是百口大家的味道。而同吃着“百家饭”的军娃们,从此便有了一种不依赖血缘来维系的真情。
谁说部队里只有直线加方块的枯燥?大院里的奇闻乐事编织出军娃们的欢声笑语
受父辈们的影响,大院里的孩子都有种尚武情结。各家各户的男孩儿人手一把BB弹手枪,见面就爱玩打仗的游戏。
那年冬天,我们密谋攻山头,谁把赤旗插在楼前的假山上,谁就是大将军。至于用意,用现在的话讲,叫“刷存在感”。
“布谷!布谷!”夜色降临,鸟叫为号。按照既定方案,“侦察参谋”龙龙上前与哨兵攀谈,想方设法吸引对方注意力,另一边,则由“总指挥”毛孩带队,伺机“闯关”。
谁知,龙龙爸加完班回家,恰巧遇见鬼鬼祟祟的龙龙,二话不说,朝龙龙腚上就是一脚。被拎在半空中的龙龙边哭边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毛孩见势不妙,撒丫子逃跑了。群龙无首,行动宣告失败。
这件事后,龙龙名声大噪,取代毛孩成为孩子们的“头头”。而《从军行》则成为我继《静夜思》和《悯农》之后学会的第三首唐诗。
在部队大院里似乎特别容易结下“革命友谊”,有与男孩子的肝胆相照,也有与女孩子的两小无猜
我的邻居月月,是个精灵古怪的丫头,特招院里大人的喜欢。而我却老实巴交,加之生得细皮嫩肉,叔叔阿姨老管我叫“唐僧”。
一次,我正在楼下拿放大镜烧蚂蚁玩,遇到了最爱逗小孩儿的刘叔。只见他拿钥匙在地上画了个圈儿,冲我厉声喊道:“唐僧,给我进圈儿里,老实待着!”这不大不小的玩笑可把我吓坏了,只好乖乖地蹲在圈儿里一动不动。正当我无助时,月月从大树后头“噌”地蹿了出来,大声向刘叔喊:“你再敢欺负他,我就告诉我爸,让你五公里不及格!”月月的爸爸是司令部的参谋,每季度机关干部体能考核都由他们组织。刘叔叔又气又笑,大步流星地走开了。
不得不承认,打那以后我对月月有一种莫名的依赖,一起外出玩耍时总是紧紧地攥着她的小手。后来,我妈很“不厚道”地把我这个小秘密在大院里宣扬了开来。从此,与她的“绯闻”直至我17岁上大学前都没有断过。
多年以后,早已长大成人的我们虽说有人风光,有人落魄,但相携相扶的好传统一直都保留着。大家并不因境遇的不同而改变对昔日玩伴的态度——“兄弟,有事您说话,一个字——帮!”
部队里的人和事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强大的教化功能,让我们懂得了何为责任和使命
大院里有个事儿曾让我一度觉得不理解。为什么家属骑车通过岗楼时,总要把腿绕过后座,单脚点地,再跨回去蹬车通过?我跑去问我妈。我妈反问我:“叔叔为我们站岗累不累?表示尊重该不该呀?”噢,我懂了。
叔叔们是可爱可敬的,但我们还是时不时爱搞个恶作剧。有一次,我们在训练场的单杠下面精心构造了一个陷阱。一个战士来了,还没上杠,就跌了进去。远处,我们放声大笑。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叔叔原本就有旧伤,这次又崴了脚,加重了伤情。门诊部的医生问他是怎么伤的,他只说是自己不小心。他当然知道是我们这帮小屁孩儿干的……为叔叔一个多月不便走路,我们内疚了好久;为叔叔大人大量、不爱告状,我们更感动了好久。
记不得哪年,某地发生恶性事件,各单位的官兵奉命在大院集结,登车出发。我们静立路旁,目送一辆接着一辆的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此时,没有一个小孩儿打闹嬉笑。在那种凝重的氛围中,我隐约感受到了正义、责任、荣誉和使命。
“叔叔,叔叔,爸爸说你不穿军装了,你是不是当逃兵了?”已经走下讲台的乐乐睁大眼睛望着我,像是在质问。这冷不丁的一句话,让我从童年的梦中惊醒,回到现实。
是啊,为什么转业?生在大院,长在大院,接触的人和事全都有关大院,军娃身上打着深深的兵烙印,以至于兵心的萌发是那样的顺其自然,以至于选择军旅是那样的天经地义。
我没法向乐乐解释“三十万分之一”的完全含义,红着眼睛问这个生在新时代的军娃:“乐乐,你长大后要当兵吗?”
“那当然!”乐乐不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