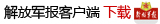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一部独具文采的里程碑作品。该书见证了一位共产主义者的诞生。80年前一位青年记者的“诗与远方”,绝非如今80后、90后眼中的清新背包游、浪漫自由行。今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文,一起缅怀这位新闻战线的前辈,一同品味他的“诗与远方”。

《中国的西北角》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中国已久,全民抗战一触即发;国民党则全力“围剿”红军,共产党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一个名叫范长江的年轻人此时尚未走出书斋,却因“新闻救国”的理想身兼《大公报》特约通讯员。1935年7月,他离开成都出走远方,开始了一次考察旅行,所写沿途见闻之后结集出版,成为一部独具文采的里程碑作品。
范长江后来讲,他当年的西北之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带着这样两个问题,他踏上征程,想不到的是,这一走竟走了4000里、10个月。他先是按图索骥,循着红军去往江油、平武、松潘,翻越祁连,绕过贺兰,之后又将脚步迈向更西部的敦煌和更北部的包头。他只图揭露真相,无意创造历史,却成为在国内报纸上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据后人考证,《中国的西北角》比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早半年,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最早的中译本早一年半时间。
《中国的西北角》记下的是行者范长江的一次壮游。悲壮多过壮美——测算下来,范长江每天最少要走40里路,且时常是在“马不能行”“尽在悬壁”的路上踽踽向前。“漠漠穷边路,迢迢一骑尘”,他行走在荒漠草原,目之所及皆是“败瓦颓垣,残梁断柱”;他趟过“往往陷死人马”的烂沼泽,“滑倒数次,满身污泥”;过雪山时遇“只有天在上,嶙嶙万山低”之景,叹喟“俨然如入森罗地域,阴寒彻骨”;甚至,为了验证徐向前部士兵过涪江冻僵而死的传说,他不惜以身试险,亲自下水……范长江的足迹及于川、陕、青、甘、内蒙古五省,国民党统治下的最黑暗的乡镇、红军经过的最险远的村落,都是他的目的地。“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且行且写,行程有终而行者无疆。
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我们发现范长江亦是一名自觉的学者,考与察贯穿他的旅途始终。凡所到之处,人文地理烂熟于心,历史典故信手拈来。一篇不长的纪实作品往往涉及不止政治、经济、文化之一方面,还有对宗教、交通、水利、农事等知识的介绍,其笃学好古、博闻强识可见一斑。写大夏河藏地男子终日念佛,不事生产,尖锐指出清代统治者鼓励发展黄教而误藏;写东南人士对于西北气候的偏见,提出洮河沿岸的岷县可参照四川平原“灌县形式”开渠引水,不必尽种鸦片;为了探明南坝“古江油关”地名的由来,奔波多地求教于专精蜀汉史地的专家,最终给出“权威之版本”…… 亦叙亦论、情景交融,除了做自然环境的描写,史论、政论也摄入笔底,或洋洋洒洒、纵横捭阖,或三言两语、意到笔随,不可谓不取精用弘、厚积薄发。
在没有互联网、甚至通信都困难的年代,范公靠眼观、耳听、口问得出大量事实和数据,对国民党统治下西北地区经济的凋敝、民族的压迫、宗教的纠纷、军阀的争斗和日益深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危机,无不予以入木三分的揭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笔触始终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记者远不仅仅是记录现象、描述事件之人,从某一现象某一事件漫延至对国家危亡的担忧和黎民百姓命途的悲悯,试图探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才是范长江作为记者的更大职责之所在。他所处的时代,各利益集团混战不堪,他却事必躬亲,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力求每一篇报道公正、真实。范公当年写鲁迅“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不正是对自己的写照吗?
《中国的西北角》见证了一位共产主义者的诞生。与其说范长江进行的是实地考察之旅,不如说是一场求真解惑之旅。他意识到,“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他的行程有数处与红军长征线路重叠,有时红军刚突围成功撤离,他就到达现场,报道实况,并分析时局。他得出结论:“(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的部队走向之)军事变化,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正是这次西北之行给出了范长江心中两个问题的答案,使他真正看清了中国未来的出路,真正成为一位端笔为戈、蘸血为墨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书读罢头飞雪。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更是一部厚重的大书。80年前一位青年记者的“诗与远方”,绝非如今80后、90后眼中的清新背包游、浪漫自由行。他的“诗”是救亡图存、探求真理的志愿,他的“远方”是祖国广大的西北地区。负重前去,在那里西望,他最终寻得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