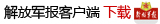陈振鹏
文汇报:上海历史上作为中国的出版重镇,出版社之间复杂的联系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很多人感到好奇的是,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着怎样的历史关系?
高克勤:要说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渊源,就不得不提“中华上编”。1958年6月1日,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上编”,后来一段时间又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纳进来,都由上海市出版局统一领导。“文革”中,上海市出版局及下属出版社包括“中华上编”在内,都被撤销了,重新成立一个“大社”,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大社”撤销后,又恢复了各出版社的建制。1978年1月,在原来“中华上编”和“大社”的古籍编辑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老被任命为社长、总编辑,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了。
“中华上编”名义上是中华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但两者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现在仍然有很多出版界后人不太理解两者的关系。在古籍专业出版领域,我喜欢称它们为“花开两枝”,从专业古籍出版的角度来说,“中华上编”和中华书局是同时起步的。
怎么理解呢?众所周知,中华书局历史很悠久,起步于1912年。1950年代初,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改组为财经出版社,直到1958年才明确为古籍整理专业出版社。因此,它的百年历史中,前40多年就跟商务印书馆差不多,是一家综合性的出版机构。还有一点就是,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辉煌,多数在1958年以后。因此,从专业古籍出版的角度来说,“中华上编”和中华书局是同时起步的。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在1956年就是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了,从古籍整理出版的角度来看,古典文学出版社的发展算更早些。
我曾经写文章披露了“中华上编”与陈寅恪先生商讨其著作出版的往来书函,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随后也发表文章,讲述中华书局在约稿上做过的尝试和努力。在出版陈寅恪著作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华书局与“中华上编”当时各自的编辑出版特点。徐俊尤其表示,对比两者的处理方式,他非常钦敬“中华上编”前辈的胆识与果敢,从中也能体会到当年京沪两地出版环境的差异。
其实从1958年开始,两家就有了明确分工,“中华上编”专做文学,中华书局以语言、文字、历史、哲学为主。1978年以后,两家共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开始关注各方面,但文学依然是重点。我1986年进社工作时,一共有6个编辑室,文学占3个,文学编辑就占编辑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从古典文学出版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正好60个年头。可以说,我们得以立社,就是因为有李俊老这么一位特别爱好、重视古典文学的创建者。他尤其珍视人才,网罗了一批在古典文学方面颇有专长的编辑。从古典文学编辑组延续到古籍出版社的,还有前总编辑钱伯城及王勉两位先生。钱老今年已经95高龄,是《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里最年长的作者。王勉先生前年年底离世,享年98岁,他更为人熟知的是晚年用“鲲西”之名,在《读书》《万象》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谈学术、艺文,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华上编”期间,有几位岁数大、资历深的老先生,可以说是编辑室里的执牛耳之人,其中的裘柱常、吕贞白、刘拜山、于在春四人,1960年代被上海市出版局批准为编审,负责稿件审读,称为“四大编审”。这些老编辑、老出版人从事编辑出版的时间都很早,进社之前就在做相关工作,比如裘柱常、刘拜山早年就分别做过上海新闻报馆和《大公报》的编辑。李俊老用人注重看学术成就,有些还是在历史上所谓“有问题”的人,像吕贞白、金性尧等,还有特约编审瞿蜕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