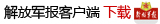在这个各种超凡想象力都能在文艺作品中尽情实现的时代,真实反而显露出更加难以替代的魅力。我想到了2015年6月去世的克里斯托弗·李爵士,他最为大众所知的事迹之一是在《指环王》系列电影中扮演过白袍巫师萨鲁曼。老人去世后,他那堪称“开挂”的人生经历随即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其中浓墨重彩的一段,便是他曾作为英国特种兵在北非战场直接跟隆美尔指挥的德军交过手。这样一段轶事曾广为流传:《指环王》第三部中有一场戏,是萨鲁曼在高塔顶端被助手从身后用刀刺死。当时彼得·杰克逊导演告诉李要发出“啊!啊”的声音,不想李却一脸不屑地打断了杰克逊:“被捅的那个人没办法喊‘啊!啊’,而是会发出类似‘呵、呵’的短促音”。杰克逊对此心悦诚服。后来观众在银幕上见到的这一场戏,被称为是电影史上最写实的刺杀场面之一。至于克里斯托弗·李为什么会有这种知识,大家结合他的经历,自然能够意会。
即使在以幻想为基本构成的艺术作品中,“来之有据”的信任感,依然能撩动观者的兴奋神经;因为对“真实”的信赖和热情,始终是铭刻在人类古老的审美基因里的。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真实性”已不仅仅局限在轶事和细节的程度。一种对宏大历史的全新观照方式,正在“非虚构写作”的旗帜下流行起来;它有别于面孔严肃的正史,又与“借杯抒怀”的历史小说写法不同,而是将还原历史的真实性追求、扎实负责的史料工作和文学性的笔法情怀结合起来,将我们所熟知的大历史中那些末梢神经式的记忆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近期,一批战争题材非虚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反响,如彭荆风的《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丁晓平的《1945·大国博弈》、余斌的《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等。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重塑了世界格局、影响延伸至今的战争,我们的印象大多来自正史(主流媒体或学校课堂)以及影视作品,也即宏观化的全景论述及传奇性的民间想像。而这类非虚构作品的出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读者对历史“末梢”的认知空白。彭荆风的两部著作细致全面地再现了中国远征军那段曲折悲壮的历史,重新照亮了抗战大历史中一段浓墨重彩却长久冷寂的记忆。丁晓平的《1945·大国博弈》则展示了铁血战场背后的政治角力,在“另一半二战史”的叙述雄心之下,作者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战争幕后大国间的政治战略较量——某种意义上,这些炮火背后的隐秘历史,比战争本身更加直接地塑造了我们今日的世界。
比具体作品更值得关注的,是写作现象的浮现。如前所述,“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正在于开启了一种角度新颖、充满温度、“末梢神经”式的微观考察。真实、细微、从熟悉经验中激发惊讶感的能力,无疑是“非虚构写作”触动文坛兴奋点的原因所在。军旅文学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当它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与“非虚构”大潮相遇并焕发光彩,势必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如果说以往常见的历史叙述类似于沙盘复原或广角镜头,其自信力来源于高瞻远瞩、鸟瞰全局式的宏大情怀,那么非虚构式的历史写作,则更像一台显微镜:它通过呈现半透明皮肤之下,那些血红细胞的奔流或阻塞、神经元的舒展或抽搐,来折射整个机体的运行和反应。
广角镜与显微镜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但一种细致入微、文学色彩浓郁而又富有人文关怀的战争历史叙事,的确填补了人们阅读记忆中的某些空白,也十分符合当今读者的审美品味,使读者得以触摸到那些散落阴影甚至布满划痕的历史侧面。一波三折的悲壮战事,这是历史袒露给我们的表层图景。波折背后的委屈与不甘,却往往作为旁逸斜出的杂音,被“修音师”们从历史的主旋律中剪辑掉了。当它们在时过境迁后重新浮出水面,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无限慨叹。
《1945·大国博弈》一书中,美、苏、英三国的暗中较量,更是主流历史想象中很少被触及的幕后隐秘——1945年二战胜利前夕,那奠定了新世界基本秩序的几大会议,竟是以一次次的揣测谋算和利益平衡开道;而历史书上大国元首并排而坐的照片,背后也藏着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战场到谈判桌,作家的心与笔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与当下材料查阅的便利以及历史档案的解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或可算是当今读者一份全新福利,也是这类写作得以打开新天地的重要原因。而比内幕资料和数据细节更古老的,则是历史动荡中被不断擦洗着的人性之光,这是《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一书吸引人之所在。相比于军人的搏杀和政客的谈判,知识分子的抗争和坚守或许有些太过安静平淡,却也以自己同样有力的方式,展现了战火之中人性的坚韧、美好与高贵。
从不同侧面展开的历史讲述,让尘封日久的往事在各自的维度上同当下读者的心灵产生了共振。与一般虚构类作品不同的是,这种共振来自于最直接意义上的“事实代入感”——相对于小说擅长在“可能性”的世界中制造自己的艺术张力,非虚构叙事则充分借助了“已然”世界的力量,它的吸引力有赖于证据确凿的“事实”。每一个人物都是曾存活于世的,每一场战斗都有细节可查;简而言之,它们惊心动魄,因为一切都真实发生过。真实本身便是力量,有些时候,它甚至约等于说服力本身。
以《旌旗万里》为例,书中随处可见详细的数据对比,包括攻守方各有多少兵员、手里有多少杆枪(有时甚至精确到武器型号)、战场周边地形如何、相关部队刚刚经历过哪几场战斗(这也是作者将不同战斗场景连缀在一起的重要方式)、以及体力状态与士气状况又是怎样等等。在“非虚构”作品中,这种扎实负责的史料工作,本身便是叙事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不同于纯粹的史学著作,这类作品“史”的一面更多体现在以事实说话的精神立场上,讲述的腔调却可以是个人化、文学化、艺术化的。如同彭荆风在一篇访谈里提到过的,纪实作品如果脱离了文学性,那么再翔实充分的素材,写成文字也难免会有精无神。运用文学化的手段去再现场景、故事,将日记、文件、采访等素材同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结合在一起,赋历史之声以抑扬顿挫的语调,这是“非虚构”写作或者说纪实文学的成功之道。
谈到真实性与艺术手法的关系,我想到了近年来饱受诟病的“抗战神剧”。过于荒唐的虚构,塑造出无数“弱智化”的敌人,也在不经意间消解了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气概绝非体现在砍瓜切菜般的历史意淫之上,而是建立在血与泪的悲壮现实之中:即便对面是横扫东亚的王牌师团、即便需要跨过战友的尸体甚至捡起阵亡者的枪,我们也一定会战斗到底。《旌旗万里》中的这一幕令我无比动容:据一位远征军军官回忆(作者特意注明了回忆人的姓名身份),当他们在反攻阶段重新打回到吞噬过无数战友生命的野人山附近,夜晚哨兵常会在营地外看到众多徘徊着的模糊身影。战士们猜测那是惨死在山里的战友们的幽魂。有一天深夜,当人影再次出现时,哨兵大喊:“我们是来为你们报仇的,你们安息吧!”人影忽然就不声不响地消散了。这当然是文学化的手法,即便有口述史作为依托,也更像是小说的情节。但参照作品先前描述过的远征军退进野人山时的真实惨状,这样的情节便丝毫不觉刺眼,甚至令人唏嘘喟叹。当作者终于写到远征军势如破竹反攻回来,那种激昂而悲壮的英雄气概才彻底喷薄而出。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小说、电视剧中的虚构桥段更精彩有力、更富有人性的美感和光彩。兼具力量与美感的非虚构写作会为这个承平日久的时代注入更多的英雄血气和崇高精神。
(《解放军报》2016年10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