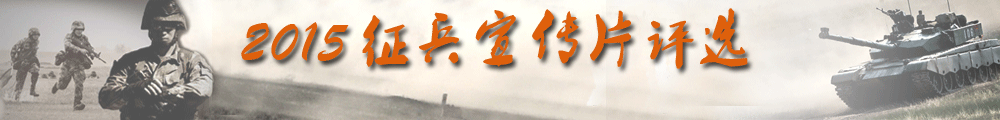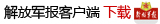肖洛霍夫:刀尖上有着对敌人的恨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同时代的在另一个战场上的肖洛霍夫。
这位俄罗斯的著名作家生于1905年,比丁玲小一岁。1928年,在他发表《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时,丁玲也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1932年,肖洛霍夫正式成为联共(布)党员,丁玲也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卫国战争爆发后,肖洛霍夫携笔从戎,以《红星报》上校记者的身份走上战场,到达西战线斯摩棱斯克一带,随后又到斯大林格勒前线,直接从参战部队的战壕和掩蔽部里汲取材料。他所关心的是战争中苏维埃人的性格和心理,把他们在巨大考验面前所显示出来的精神上的坚定性,他们的伟大及建立功勋的决心表现出来。时过一年,肖洛霍夫就在《真理报》和《红星报》同时发表短篇小说《学会仇恨》,“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的野兽面孔,竟能达到如此兽性和野蛮的极限。”小说的主人公格拉西莫夫中尉作为德军的战俘,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但他没有哀怨。他与丁玲小说中的“老太婆”一样,成为从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折磨中锤炼出来的坚忍不拔的英雄。
正如同肖洛霍夫的小说《学会仇恨》中的橡树是俄罗斯民族不可摧毁的精神化身一样,丁玲《新的信念》里大海上的巨浪乃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象征。虽然两位作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面对的都是共同的敌人法西斯;虽然两部作品发表的年份不同,但都是在反侵略战争的初始阶段;虽然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份不同,但都表现出了共同的磨难和人物性格;虽然两个故事的结构和情节不同,但都揭示出了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格拉西莫夫中尉望着阳光灿烂的林间小路说,“只要我们在心脏停止跳动前始终怀着对祖国的爱,那么,我们的刀尖上也将永远有着对敌人的恨。”这也是两位作家相距遥远,作品又如此相近的根本所在,都有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
抗战作品的反思与再评价
丁玲和肖洛霍夫笔下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战争最残酷、最激烈、最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文字,却永远留给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阅读,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关于作家的位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作家,他(她)的位置在哪里?丁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到前线去”!1931年上半年,丁玲丈夫胡也频惨遭杀害、日本侵略者在蚕食东北的同时,将炮舰驶向东海,丁玲毅然向党组织提出到江西苏区去。但中央研究丁玲暂留上海,创办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直到5年之后,丁玲再向党组织提出去延安,终于踏着初冬的雪,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到前线去”或“留在后方”作为衡量一个作家对民族解放事业贡献的惟一标准,但是,处在血泊中的民族需要用文学艺术的感召力来动员和凝聚抗敌的意志,处在炮火中的军队需要塑造英雄的榜样来激励和鼓舞决死的血性,那些直接来自前线裹着硝烟和浸染着血迹的诗文、戏剧、音乐、图画,将会爆发出比大刀、梭镖、火炮更具威力的精神力量,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肖洛霍夫在同法西斯进行恶战的危急时刻来到战壕里与战士们交谈,说,“我想写你们是怎样为祖国而战的,所以我才到战壕里来了,向你们学习,了解战场的生活和真人真事。”这就是作家的位置,也是丁玲为什么要响亮喊出“到前线去”的原因所在。假若光未然在抗战爆发后没有东渡黄河、转战吕梁、跋涉延安,他还能写出“为抗战发出怒吼”的《黄河大合唱》吗?假若范长江没有抵近抗日前线,他能写出《台儿庄血战经过》《血泊平津》《西线风云》等战地名篇吗?假若丘东平没有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热河抗日战争,他能写出《第七连》《长夏城之战》等激发军民同仇敌忾的时代报告吗?假若沙汀没有随八路军奔赴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他能写出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吗?还有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碧野的《滹沱河夜战》、艾青的《起来,保卫边区》等等,都是作家在燃烧着抗日烽火的焦土上耕耘收获的成果。前线需要文艺,作家不能远离斗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
关于作品的评价。对同一个作家或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大相径庭,原因自然复杂多样,但究其主要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不同的视角差异。在前线或后方、在根据地或亭子间,地域环境不同,阅读作品的感受不同,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结果也会不同。二是派别不同的认识差异。在当时以至后来一个时期,中国文学界也包括进步作家组织,既有受文人相轻的传统劣习影响,又有受宗派主义影响,把人际交往中的亲疏恩怨带到了对作家作品评价中,不能实事求是。三是标准不同的审美差异。大敌当前,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最需要什么?衡量文艺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分歧在于战争文学特别是战争进行时的文学,要不要把巩固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敌的战斗力作为惟一正确的标准。正如丁玲为《红军中华副刊》写的编后所言:“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当然,身处火线的作家不可能像在大后方那样从容写作,只有在战斗间隙采访,深夜坐在火边写作,直接而简练表现战地生活。对此却有着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文学性、时代性的获取,不免要以文学性的部分丧失为代价”,“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这个新文学运动里的顽症,由于战争以来政治任务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滋长了”。丁玲坚持认为,“新文学的花朵是染着烈士们的鲜血的。”地处卫国战争前线的苏联作家,与丁玲的态度高度一致。“在战争的路上仓促写成的,用飞机运送的千百篇素描紧接着前线的事变立即出现在各地报纸上,诗和文章在战争最艰苦的时日号召同敌人斗争,描绘出苏维埃军队的英雄伟绩。”肖洛霍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作家更多地对社会负责,还是更多地对艺术负责?”他回答:“对社会负责。艺术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岁月斗转星移,历史回声犹在耳边,值得我们在今天认真反思。
关于文学记载。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对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作品评述是不够的,这与大批进步作家奔赴抗日前线的斗争历史和文学实践是不相符的,像丁玲在抗日前线创作的小说、散文都未在文学史中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这是因为作品艺术上有些简陋或粗糙而在文学史上“缺席”,是不是该反问史家们自身有什么“缺失”?看看苏联或俄罗斯的文学史,他们是怎样满怀激情赞扬奔赴卫国战争前线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许多东西还是苏联作家急匆匆间写就的,许多东西还没有澄清,但是他们的书籍却都散发着那确立多年和平发展的时代空气。”“但就是在这段时期中间所写作的东西里,苏联作家也替将来保存下对于当代巨大历史事变、对于为拯救世界脱离法西斯党徒所带来的黑暗而斗争的一代英雄主义的活的概念”。对比之下,我们作何感想?面对那些不惧流血牺牲站立在斗争最前沿的前辈作家,我们应从他们身上感悟并传承什么,这或许是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