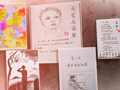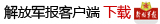汶川地震发生后,本文作者前往抗震救灾一线采写稿件。
“弃车!步行!”来不及多想,带队的某集团军熊副军长果断作出这一决定。
次日天刚亮,当我们沿着唯一一条可通行的深谷向19公里外的县城奔袭时,几名老乡慌慌张张从峡谷里奔出来。原来,连续不断的余震造成大面积山体滑坡,在12日大地震中遭受到了灭顶之灾的陈家坝乡,又有几个村民小组被淹埋。
我们事后看到的情景比村民介绍的还要严峻:乡政府所在地90%以上的房子已经倒塌,歪歪斜斜站立着已是墙体开裂,屋顶通天,废墟中不时传出急切的呼救声。几名乡领导语气急促地介绍说,目前初步查明,乡政府所在地至少有500遇难或失踪。而且,因山体下滑被阻断河谷,在距此几公里外形成了一个后来才知道叫堰塞湖的小湖泊,余震随时可能造成决堤,附近防震棚里的近千名村民危在旦夕。
就在他们介绍间,对面两座大山上,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排山倒海般涌下了约三四百米宽的大塌方,把山下还幸存的十几间房子也掩埋了,大滑坡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
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门口,七八个不像是一家人的村民端着方便面碗木纳地把半生不熟的面条往嘴里送。一个姓苏的中年女子指着滑坡的地方对我说:“记者同志,惨啊!我们这个院子里住着3家人,昨天就死了12人,还有3人干活时被埋在那山下面,八成是死了。”给我们带路的一个姓马的民兵接上说:“那是一个鱼塘,昨天那里埋了二三十人,我母亲也埋在那里。”他们说这话时,似乎不像我想像的那么惊恐。一天多来,“见怪不怪”的灾难似乎使他们有几分麻木了。
那一刻,我几乎失去了继续写新闻的勇气:眼前惨不忍写,我真不敢面对现实!
那一刻,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无知的。在赴灾区的军列上,我通过在昆明随我学习的班晓、黄庆西查到了《世界百年历史上的大地震》的相关资料,传到我手机里:
1906年美国旧金山地震,里氏8.1级,死亡人数约2000多人。
1920年中国甘肃地震,里氏8.5级,死亡人数20万人。
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里氏8.3级,死亡人数逾10万。
1960年智利地震,里氏8.5级,为20世纪最大的地震,1000多人死伤或失踪。
1976年中国唐山地震,里氏7.8级,造成24.2万余人死亡。
1985年墨西哥地震,里氏8.1级,造成1.2万人死亡。
1989美国洛马—普雷塔地震,里氏7.1级,造成约62人死亡。
1994年美国洛杉矶北岭地震,里氏6.6级,造成约58人死亡。
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里氏7.2级,造成5502人死亡。
眼前的情景令我吃惊,与这些地震比,汶川的伤亡肯定不会少。一千、一万……甚至还是更多,我不敢想象。
“就地疏散村民,抢救废墟中的群众!”就在我“不敢想象”中,熊副军长果断下达命令。对熊副军长的这一命令,不光随行的参谋,就连记者也为他捏了一把汗:就地救灾不仅会延缓赶到县城,还会冒着决堤和山体滑坡造成部队伤亡的危险。有人曾提出异议。但熊副军长一咬牙:“救灾就是打仗,如果头顶西瓜走路,那就是失职,不是对人民负责!”
“责任”,让熊副军长作出了这一果断的决定!
当时,部队面临的情况,非亲历者理解不了其艰辛。由于交通、通讯中断,加之受地形限制,部队简直如置身“孤岛”。熊副军长根本无法将部队行程向后方指挥所报告。在得不到前方指示的情况下,头脑中唯有“责任”指挥着怎么办。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17-18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历险记》中的不幸:
“我流落在一个可怕的荒岛,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
可以说,老天单单把我挑了出来,让我与世隔绝,让我经受苦难;
我远离人类,孤苦伶仃地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
我没有什么衣服可以遮身;
对于生番或野兽的袭击,我没有什么防御手段;
没有谁能来跟我说话,或者来解救我。
……”
突然间,我想到自己背包里装着的海事卫星。那是报社为方便传稿,临时配发给我的。于是,选址,找信号。但由于地处是山休滑坡,一连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一个有信号的地方。那激动啊,如同在大海中抓到一根可驶向陆地的斧头。
很快,情况终于报回到后方指挥所。
这下,我仿佛又看到了鲁滨逊在自己日记中记录下的幸运:
“……老天既能显示奇迹让我免遭一死,也能救我脱离这环境;
……但我还在热带,有衣服也不会怎么穿;
但在这个岛上不像我到过的非洲海岸,没有会伤人的野兽。要是船在那儿出事,又会怎样呢?
但老天大显神通,让船漂到海岸附近,使我得以取来大量的必需品,其中有的够我用上一辈子。
……”
就在情况报回后方指挥所的同时,这支部队也在“责任”驱使下,兵分两路,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一路转移群众,一路在废墟中救援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