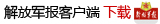(六) 崇善堂等慈善团体埋葬尸体的数量“不可信”
阿罗健一称,他最近发现了“新”的史料,是一份《民国24 年度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内中对崇善堂的业务记载为:施舍、救抚、保婴等项。于是乎,阿罗以为发现了“新大陆”,称这份报告证明崇善堂“没有从事葬仪和掩埋的业务”。另有一份《中华民国27年度南京市概况》,其中崇善堂的业务也“与处理尸体无关”。阿罗凭着这些“新资料”就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即,因为崇善堂没有掩埋尸体的业务,崇善堂埋葬尸体的数量自然“不可信”。
(七) 日军杀害“便衣兵”属于战斗行为
“虚构派”对便衣兵的定义是,打扮成普通民众,但没有放弃抵抗、甚至发动暴乱的中国军人,屠杀“便衣兵”不违反国际法,属于“正当战斗行为”。
(八) 中国溃兵杀害和抢掠了中国民众
小林善纪在《战争论》的漫画里,描绘了一批国民党官兵“化装成日本兵,大肆掠夺、强奸、放火”的画面,声称是“中国军队把责任推给了日军”。
(九) 污蔑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多是“伪造”
其“代表作”是东中野修道等人编写的《检证南京事件的证据照片》(草思社2005 年) ,他还成立一个“南京事件研究会照片分科会”,组织人马专门对证实大屠杀事件的143 幅历史照片(另一说139 幅) 进行“考证”,最后得出结论竟是:现已公开的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多是“伪造”或“拼接”的“, 能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枚都没有”。那么,他们否认这些照片的“根据”又是些什么呢?准确地说,不过是猜测和武断。比如:一张被砍下头颅、嘴里叼着香烟的照片(当时西方媒体刊载了此照片)。“虚构派”认为,这张照片是被“嫁接”的,根本不是真实照片,理由是‘日本从江户时代就废除了斩首制度,在昭和初期更不允许实施这样的野蛮行为”;还有一张日军士兵一手拿刀,一手提着一名中国人头颅的照片,“虚构派”称,照片中的日军士兵是海军装束,但海军并没有参加南京攻略战,所以照片是“假”的。一名口本士兵高举洋刀,正欲砍下一名跪在地上的中国人头颅的照片(此照片收录在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印的《日寇暴行录》中)。“虚构派”称,此士兵仅穿一件内衣,而占领南京是在12月份,南京的气候不可能穿得如此单薄,因此认证这张照片是“赝品”;一名日军举刀正砍一位蒙着眼罩的少年照片,“虚构派”说,握刀的姿势不对,“不是日本剑道的姿势”,所以诬称“举刀者是中国军人”。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就是用这些“证据”或诡辩来否认照片的真实性。
“虚构派”一面否定大屠杀照片的真实性,一面搬出当时日本随军记者为粉饰太平,所拍照的日军士兵给中国人理发、日军“保护”农民在棉田劳动、日本军医给中国人看病等照片,称这些照片才是“第一手资料”,企图借此说明南京秩序的“安定”,日军军纪的“严明”等,但明眼人一眼就能洞察其中的虚假。
(十)攻击和污蔑被害人和证人
东史郎案件的背后,有“虚构派”作祟是众所周知的,东史郎案件败诉后,“虚构派”欢呼雀跃,竟宣称此案的胜诉证明南京大屠杀事件“子虚乌有”。还有,以松村俊夫为代表的“虚构派”为了全盘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存在,竟肆意诬蔑李秀英、夏淑琴是“假证人”,做的是“假证”,于是引发一场关联南京大屠杀是否真实存在的诉讼,最后松村等人以惨败而结束了这场诉讼。除上述观点外“, 虚构派”还吹嘘攻占南京的日军“军纪严明”;马吉牧师的证言和记录片是“假造的”;朝日新闻社“对中共一面倒”,应该对“伪造”南京大屠杀事件负责;张纯如的著作是“反日宣传的伪书”(藤冈信胜语) 等等。
以洞富雄、藤原彰、姬田光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江口圭一等人为代表的南京大屠杀“肯定派”学者,顶着右翼社会的压力,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考察和研究,一致肯定东京国际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审判,认为日军的确在南京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应该向死难者及其家属赔偿谢罪。不过,在被害人数方面,由于受资料和时空的限制,以及统计数字的难度,他们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被害人数的认定不尽一致。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的开拓者洞富雄先生在《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指明,日军在南京城内屠杀中国军民不下20 万人之多。藤原彰支持这一观点,并且指出“, 被不法杀害的牺牲者远远超过战死者”。笠原十九司是位严谨的学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他根据现行掌握的史料认为,被害人数当在“十数万到二十万人左右”,但是,他又指出“, 随着史料的公开和被挖掘,被杀害的人数尚有增加的可能”。 吉田裕的研究认为,“至少在十数万人以上”,“特别是南京近郊农村被杀害的人数难以统计”。姬田光一、江口圭一、井上久士等学者的研究结论是“至少十数万人以上”。评论家高崎隆治认为,南京被杀害人数在20 万人左右。
以上可知“, 肯定派”学者大多认为南京事件受害者人数在20万人左右,他们之所以在被害人数的认定上不尽统一,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时间久远,统计数字有相当的难度;二是考虑到东京审判的结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宁可把数字缩小,也不枉加推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治学之严谨,中国学者应该理解和体谅他们的立场及治学态度。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