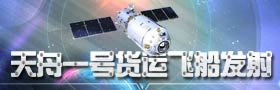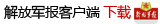“涂饰之文”最无益
■贾世江
宋太祖赵匡胤要扩建东京城,在赵普的陪同下,亲自到朱雀门去察看。远远地看见城门上题写4个大字:“朱雀之门。”太祖问赵普:“明明是‘朱雀门’,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之’呢?”赵普答道:“‘之’字是语助词。”太祖听后一笑:“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之乎者也”这一套,多为官话套话,只鼓捣词而不办实事,闭门造车,毫无价值,助长了官场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的恶习。晚清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感叹:“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
官话往往说得冠冕堂皇、义正辞严,但都是“不打粮食”、不击要害、不明时限的空话套话。封建官场常靠此类官话,滴水不漏地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类似“殊与体制不合,所请毋庸置议”“例章所格,未便转详”“务须筹酌妥当,在容请示办理”云云,三言两语,就可以将各类事务打发,叫你急不得、恼不得。
据《梦溪笔谈》记载,庆历八年夏,黄河河北方向决口,适逢掌管此事的使臣来京述职。宋仁宗召见他:“河北的水灾怎么样了?”使臣回答:“怀山襄陵。”意为洪水包围了高山,淹没了丘陵。又问:“群众怎么样了?”回答:“如丧考妣。”意为像死了父母一样悲伤。这位使臣面对皇帝的问询,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但对具体受灾、赈灾的情况一无所知,显然没有把灾情民瘼挂在心上。宋仁宗明确要求:“今后这些人上殿报告事情,一概实话实说,不得搬弄辞藻。”
“涂饰之文”最无益。应该说,历代统治者不乏头脑清醒之辈,敢于硬起手腕、拉下脸来进行整治。
朱元璋对茹太素的冗长之文,办法是先杖责一顿,再制定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
同样以铁腕治吏著称的雍正,对“涂饰之文”深恶痛绝,批评起来不留半点情面。比如,他在朱藻的折子上批示:“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在马尔泰的折子上批示:“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在伍格的折子上批示:“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在索琳的折上批示:“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对一支军队来说,战争是最严格的审计师。如果听任“涂饰之文”大行其道,影响的不仅是办事效率,而且注定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法国在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么一败涂地,要么付出巨大代价方才惨胜,参谋机关整体素质不高是个重要原因。富勒对此曾评论说:“当战争在1870年爆发时,我们发现第二帝国的参谋本部军官,都是一些刀笔之吏,不是少不更事之徒与军队完全没有发生过接触,就是长胡子的老人,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
军令急,军情迫,容不得半点拖泥带水。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每一次讲话、每一份命令,都可能事关战场胜败。如果指挥员一张嘴就是那些空话套话,一行文就是那些“壳如西瓜核似绿豆”的冗长之文,一重视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胜利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
宋时轮将军一次到部队调研,单位领导汇报时以“自我表扬”为主。汇报完毕,将军问:“你姓什么?”领导回答后,将军说:“你不是这个姓!”对方不解。将军又说:“你姓王,叫王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今天,我们正在深入推进改革强军,应下决心彻底与形式主义、假大空虚、繁文缛节那一套决裂。只有始终把“战”字刻在心上,像打仗那样、按打仗需要办文办电,才能在未来战场多一分胜算。
(作者单位: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工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