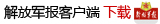今天,我们怎样做记者
■贾永
每当看到你们这样一些青春的面孔,我就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开始走上新闻之路的时候。
1981年5月,在离国境线几公里的地方的一座战时的油库里,也像今天这样,正在举办一个新闻短训班。按照计划,短训班要办10天,但是,第6天的时候,突然宣布提前结束。班上的两个年轻战士,一个要跟着步兵参加主攻战斗,另一个要跟着炮兵参加助攻战斗。10天之后,与主攻部队一起行动的小伙子牺牲在了战斗中。他叫叶永宁,刚满19岁。他唯一发表过的作品,是在他牺牲后,原广州军区《战士报》刊登的两幅剪纸;与炮兵部队一起行动年轻人,便是我,那一年,18岁。从那时起,我走上了军事新闻之路。到今年,38年。

贾永八十年代初在广西边防。
一、脚力:脚底下面出新闻,真正的新闻是走出来的!
我的采访对象就是我身边的战友,写作的素材就是战地生活。在当时,我们被称作“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前线部队大都是守卫山头,方圆几十里也没有几户人家,山路崎岖又不通电,除了极小的一块地方外,许多阵地三面都是地雷区,种不了菜也贮存不了新鲜肉菜,每天的主打菜基本上是榨菜、萝卜干、海带、罐头,外加土豆和萝卜之类。有个擅长美术的战士还创作了漫画登在了报纸上,标题好像叫做《连队菜谱》,画面上的内容是,“菜谱:午餐,萝卜白菜;晚餐,白菜萝卜”。
那时候,南部边境线上流传着一首模仿夏明瀚烈士遗作写成的战地诗,叫做:“吃苦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前线官兵也确实像战地诗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感。不过苦日子长了,也会有个别战士忍受不了。一个胖胖的四川籍姓胡的副班长属于肉食动物,平日里最爱讲的就是“来个鸡肉烧茄子咋样,最好是鸡肉多点茄子少点甚至没有茄子那种”云云。有那么一段日子接连暴雨,几个星期没闻到肉味儿,胡副班长每天摇摇晃晃执勤归来,几次定定地望着拴在坑道口的军犬呈思索状。直到有一天,当着军犬引导员的面,冷不丁地冒出了他的幻想:“如果这家伙一不小心跑进雷区,轰,咱们是不是就能吃到狗肉火锅了?”在前线,军犬可是相依为命的战友啊,何况那军犬立过战功。引导员一听急了,松了牵狗绳,追着胡副班长满坑道乱钻,恨不得让军犬撕碎了这家伙。
前线的日子倒也苦中有乐。年轻人聚在一起,多的就是力气和精力。战友们用罐头盒、炮弹筒之类养花种草美化阵地的做法,得到了上级肯定。到任不久的指导员又张罗着养鱼,对连长说,山上猪养不了,养鱼总可以吧。指导员二十出头,很想有一番作为,鼓励全连骨干“带头看到光明,带头提高勇气,一定要让大家吃上自己养的鱼”。连长是老边防,清楚山上连吃水都困难,靠积攒雨水养鱼显然不太现实,见指导员心血来潮,全连又士气正旺,也不好阻拦,还亲自带上几个兵到修坑道的工兵那里借来水泥,雷厉风行地抹了个养鱼的池子。阵地养鱼的事后来还惊动了机关的新闻干事,不过看到浅浅的池子中只有十几尾鱼,也不好描述,又不好大老远白来一趟啥也没写。那干事毕竟老道,在后来见报的短文中,用了“看到了一片的鱼”这样的描写,这让初学写作的我大受启发。想想也是,让人家怎么写呢,写“几条鱼懒洋洋地在水中漂荡”,显然煞风景;写成“成群的鱼儿欢快地游戏”,也有违事实。用“看到了一片的鱼”倒也符合场景。
1985年清明节,广州《羊城晚报》派资深记者李春晓到边防采访。当时我已经在师里当新闻干事。得知我们部队流传着这首战地诗,就让我一起寻找战地诗的作者。本来那诗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凑的,找了几天自然也没有找到谁是具体作者。不过我讲的几个故事还是感染了李春晓,她就让我把故事写下来。李春晓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但很敬业,只用一个晚上就改出了一篇出色的通讯《追踪一首战地诗》,先是刊登在《羊城晚报》头版头条,第二天又被《解放军报》在同样位置转载。战地诗由此传遍全国,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振兴中华”一起流传的口号。通讯获得了全国好新闻奖,那也是我第一次获全国奖。
1985年,我参加军队高考,凑巧的是,当年军队高考(干部试卷)的作文题目,竟然是为一篇与《追踪一首战地诗》同类题材的《热血男儿一席谈》写一篇评论。所以我写得很轻松,也得了一个较高的分数。
我1980年11月27日到边防当兵,1985年8月28日离开边防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上学,在边防部队生活了4年9个月零1天。人们常说部队是熔炉,也可以说,前线部队就是熔炼炉中的熔炉。
1987年,我从南京政治学院到中国青年报实习,正赶上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报社安排我跟着记者一起到火灾区采访。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中国新闻界最新锐也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有一批实力超强的记者。他们中有的以思辨见长,比如后来写了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张建伟;有的以深度调查闻名,比如后来参与了《雍正王朝》编剧的麦天枢;还有的以评论锐利而闻名,比如后来做了中国青年报多年总编辑的陈小川,以及后来做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如今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既勇敢又敬业,危险面前争着上。比如那次带着我到大兴安岭参加扑火报道的雷收麦、李伟中、叶研,都是有名的拼命三郎。李伟中除夕之夜在前线与突击队员一起蹲猫耳洞,枪炮声中写出著名的战地报道《战士万岁》;叶研直到年过半百之后还跟着科考队几度赴南极考察。雷收麦当时是中国青年报驻黑龙江记者站的站长,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批评报道,叫《愤怒的炖鸡》,批评哈尔滨工商人员刁难个体经营者,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大兴安岭大火灾发生后,记者们当然都争先恐后,要求去现场。既然如此,为何让我这样一个刚刚到报社实习一个星期的大学生去呢?这就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杨浪先生。杨浪当时担任中国青年报国内部副主任,他在云南当过兵,深知重大灾害来临部队肯定会冲在前面,让我这样的一个军校学员去,采访时会方便些。更重要的是,杨浪有过边境作战经历,了解像我这样上过战场的军人敢冲敢闯,既能吃苦又不怕死。杨浪对“三色”报道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是,还在我们出发之前就为报道定下了基本基调,那就是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大灾大凯歌”式的模式,要求我们透过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森林大火,探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我们的整个采访也是按照杨浪最初设定的思路进行的。杨浪后来主持过著名的财新杂志的编务工作。
这把大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又是怎样烧起来的?在大火的映照下,各色各样的人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在当时的情况下,按照这样的思路采访,按照这样的思路探求真相,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当地不少领导和机关以封闭的新闻思维实施着“新闻封锁”。
在各种限制和阻挠面前,不少记者只得离开灾区。我们四个留下来了,当时,除了雷收麦年近四十外,我们三人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而且都有过边防前线血与火中的采访经历,都有强壮的体魄。我们艰难而又充满信心地拓展着获取第一手材料的范围:火场,坟场,废墟,河套;广播员,水枪手,推土机手……白天厚着脸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晚上与灾民一起睡在四十个人一起的寒冷的帐篷里。
我们没有走。边防前线血与火铸就的“敢死队员”的精神仿佛在主宰着我们。为了维护人民群众了解社会重大事件的知情权利,为了让更多的人们观察到一个巨大的历史和社会变革前夜所显现的诸多现象,我们冒着危险坚持留了下来!
也许是从我们的行动中悟出了什么,越来越多的原来慑于某些人淫威而敢怒不敢言的灾民向我们敞开心扉直陈真情。夜里,我们行走在废墟上,一位鄂伦春族干部请我们去喝他在废墟上烧的第一壶茶;端午节,住在我们帐篷附近的母女俩用亲戚送来的两个鸡蛋慰问我们。
当我们作为最后离开灾区的记者,每人带着厚厚两大本详细记录了大兴安岭灾变的采访笔记和十几筒摄有灾区各种图像的胶卷登上南去的列车时,大火已全部熄灭。在大兴安岭地区首府所在地加格达奇,大兴安岭林管局的一位姓张的副局长居然找到了我和李伟中下榻的小旅社。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林管区将召开常委会,反思火灾和救灾。而在此之前,这位副局长是想赶我们离开的。第二天一早,当我们出现在林管局的会议室,一屋子的人自然是吃惊的。不过,也不好让我们离开。实事求是地讲,林管局的领导大都还是不错的干部,文化水平高,也比较民主,反思也很中肯。但是,当时僵化的体制和改革的滞后导致了他们沾染了很多的国有企业干部的通病。其时,林管局和大兴安岭行署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企业领导又是党政领导,既隶属于当时的林业部,又隶属于黑龙江。而大兴安岭林行署所在地加格达奇,行政归属黑龙江省,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林管局又是林业部直属森工企业,“一个媳妇仨个婆婆”。既不敢称为市,又不能叫做镇,最后只能无奈地称为加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各方利益还比较好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快发展,各种潜在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我们的三篇报道标题是《绝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后来,新闻界通常称为“三色”报道。
应该说,“三色”报道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反响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料。在哈尔滨,甚至还发生了抢购中国青年报的风潮。那位大兴安岭林管局的副局长被免职后,还给我和李伟中来信,说他曾经为难过我们,但我们的报道对他的描述还是客观公正的。他已经让正在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儿子报考了他的母校南京林业学院,继续从事林业工作。“三色”报道获得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特别奖。迄今为止各种版本的新闻教材,也都把“三色”报道作为研究灾害报道的范例。
当时就有人说啊,贾永这小子运气好,当兵赶上了边境作战,得了个新闻奖;实习赶上了大火灾,又得了个新闻奖。事实上,对我个人而言,收获最大的是,大兴安岭火灾报道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新闻观尤其是采访作风。套用一个物理学观点,在此之前我是零度的冰,但“三色”报道之后,我成零度的水了。由零度的冰到零度的水的这个变化过程需要“融解热”。对我来说,这个“融解热”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青年报》那一时期的熏陶。那样一种视党的新闻事业重如泰山的理想追求,那样一种宽松而又民主的环境,那样一种充满正义与激情的氛围,那样一种求真求细的扎实作风,令人难忘。需要指出的是,“三色”报道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比如前面提到的杨浪,他的思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具体写作也是以三位记者为主力,我不过只是尽了我的责任而已。
当然,这次报道确实让我得到了一些荣誉,比如作为实习生获得“社长、总编辑嘉奖”,据说在中国青年报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还因此常常被称作中国青年报历史上最优秀的实习生。作家韩作荣、王南宁在当时的《人民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中专门写了我和李伟中一节,叫“迷彩服与绿军装”。因为在大兴安岭那段日子,我和伟中一个穿军装,一个穿迷彩,整个县城都认识了我们。后来还有个插曲, 2016年的春节,我到中俄交界处的伊木河边防连采访,路过漠河,只有半天时间,很想找到当年在大兴安岭采访时端午节为我们送过两个鸡蛋的小姑娘,结果还真找到了。30年过去,那个小姑娘也是40多岁的人了,但一眼就认出了我。
“三色”报道已经过了整整32年。上个月媒体点评改革开放40年新闻界大事,“三色”报道榜上有名。它之所以成功,或者说之所以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公正。而这种客观与公正又来自扎实深入的采访。公正是记者的良知,落实到记者工作中,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以平等的态度与方式对待新闻事件的“当事者”各方,始终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尤其不能以一己之利代替社会的公众良知,更不能以一孔之见假冒民意替代公论。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个字,概括了在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习总书记指出,“要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但这决不意味着记者能够忘乎所以。普利策曾经把媒体视为文明社会崛起的一股强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新闻业良性运行的难度。正因如此,他提醒人们:“新闻事业的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新鲜报道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但是,一直以来,总有一些笼罩着“无冕之王”光环的新闻从业者陶醉于自身的“布道者”角色,而对履职尽责的边界难以保持清醒。
我向大家讲上述这些经历,便是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第一个方面,也就是习总书记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增强的“四力”之一,脚力。结论就是:脚底下出新闻,真正的新闻是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