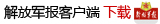德军的11月攻势发起后,战斗更加残酷了。在克林地区,德军集中了300多辆坦克,在炮兵和俯冲轰炸机的有力掩护下,猛烈冲击只有几十辆坦克的第16集团军的战斗队形。战斗从16号开始,一直进行到20号,德军却始终没能在第16集团军第316师守卫的阵地获得突破。英勇的316师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红旗勋章,第二天,这个师又被命名为近卫第8师,到了第三天,这个师的师长在战斗中牺牲了。
西方面军中的第16集团军的第107师还剩下大约300人,坦克第58师已经没有了坦克,坦克第25旅中还有12辆坦克。这个集团军伤亡太大了,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少将请求后撤。但是,朱可夫不同意。罗科索夫斯基急了,于是,越过朱可夫直接给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请求后撤。沙波什尼科夫也同意了罗科索夫斯基的请求。然而,朱可夫闻知非常生气。他给罗科索夫斯基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措词严厉:“负责指挥方面军各部队的是我!我不准你们撤退一步!”
罗科索夫斯基服从了这个在人们看来无法做到的命令,因为在他的身后,是通往莫斯科的最后一段公路。
就在这天晚上,罗科索夫斯基接到了斯大林打来的电话。
“您很困难吧?”斯大林在电话中只是这样问道。
罗科索夫斯基感到了信任,他回答说:“是的,斯大林同志,非常困难,非常……”
斯大林沉默了一下之后,说:“我理解,请您再坚持一下,我们会帮助您的。”通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清晨,罗科索夫斯基得到了增援:1个“卡秋莎”炮兵团、4个反坦克连、3个坦克营和由2000名莫斯科人组成的战斗部队。
距离莫斯科西北27公里有一个名叫红波利亚纳的地方,今天它已改名为梅季希。从这里出发,坦克最多一个小时便能抵达莫斯科城。12月3日,德军第4坦克集团军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攻占了红波利亚纳。
博克元帅及时赶到了这里,当这位德军前线总指挥登上一座塔楼,将望远镜举到眼前的时候,他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他已经在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尖顶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然而,这里是这位德国陆军元帅今生今世所能到过的距莫斯科最近的距离,也是德军最后一次看到莫斯科。
历史总会出现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1812年,拿破仑统率着浩浩荡荡的法兰西大军横扫欧洲,但在莫斯科城下却大败而归。据说,那是上帝拯救了俄罗斯,因为就在拿破仑胜利在望时,严寒突然降临。1941年的冬天,上帝又一次站到了俄罗斯人的一边。
德军对莫斯科发动的新的进攻和最寒冷的天气几乎是同时到来的。
11月13日,莫斯科地区的气温降到零下8度;2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使气温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骤然下降至零下40度。莫斯科会战中在冰天雪地中的德军官兵
地面上结了厚厚的冰层,德军的机械化部队终于又可以重新开动了。但是,把坦克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严寒,却又开始无情地摧残那些还身穿夏季军服的士兵。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冻成残废,染上了使人寒颤不止、全身无力的疟疾。越来越多的冻伤的德国官兵倒在雪地中,歇斯底里地呜咽着:“我再也挨不下去了!我实在挨不下去了!”寒冷的天气使大炮上的瞄准镜也失去了作用,燃料常常被冻结,坦克的汽油也冻成了黏糊状,必须通过火烤之后才能发动。
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这样傻,大冷天的不装备棉衣?
其实,这不是德国人傻,而是德国人太狂了。如果希特勒不那样狂妄,德国士兵不会这样遭罪的。
早在9月29日,在“台风”战役即将发起前夕,德军陆军总部根据情报部长和气象部长提供的资料,认为莫斯科地区入冬前可能连降大雨,使冬天提前到来。因而,他们向希特勒建议应抓紧时间,突击生产300万套防寒棉衣。
希特勒听完他们的建议后,哈哈大笑地说:“我相信,冯·博克元帅的士兵很快就要行进在俄国首都的大街上了。”
然而,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德军不但没有行进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反而却在莫斯科郊外的掩壕中瑟瑟发抖。一批又一批的官兵冻倒在雪地里。
眼瞅着莫斯科已是指日可下,更确切地说,莫斯科现在已处在德军火炮的射程之内,严寒却紧紧地卡住德军在各地的攻势。
而在此时,身披白色滑雪衫的苏军新的预备队却源源不断地开进莫斯科城下,接替损失惨重并且疲惫不堪的苏军兵团和部队。他们个个穿得暖暖的,足以御寒;他们的机枪披着枪套,以防止寒流的侵袭;他们的武器加上冬季润滑油,使用灵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大量威力强大的T-34型坦克群的支援。这种T-34型坦克正是为这种严寒条件下作战而特地设计制造的。
这时,博克元帅终于明白,他的部队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此时气温已降至零下40℃,他的部队冻死冻伤过半,没有燃料和弹药,坦克差不多都动弹不了,从北面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已无法实现。面对这种困境,博克元帅打电话给弗朗茨·哈尔德上将说:“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上帝加入了俄国国籍,我请示立即撤退!”
严寒大大削弱了德军的士气。而此时,一位少女的牺牲,却更加激发了莫斯科军民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