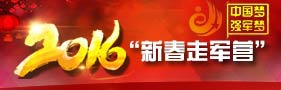一种境界
■于永军
“精简整编,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几乎每一个干部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这是回忆30年前那次百万大裁军经历,我脑海里浮现出的一句动员讲话。那时,我不满30岁,从部队调到济南军区组织部工作刚两年时间。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大家都清楚“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的含义。亦即,一夜之间将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按照军委整编方案,武汉军区撤销,分别并入济南军区和广州军区。这种情况下,尽管军区机关人员的调整面不大,但贯彻既“消肿”又“输血”的原则,也有一批人要从武汉军区输入,组织部就要进来三名年轻的同志。这意味着,原班人马中必须调出三个位置。
12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随领导下部队回来,同室工作了近三年的战友任全良告诉我,他准备走了。我说,开什么玩笑,走也轮不到你呀?他说,这是真事儿,部里已经开会研究了,他和组织处的冯处长转业,张干事交流到军里去,并已报有关部门。这个消息,让我惊讶不已。
我的惊讶是有理由的。首先,全良在我们处里的四位干事中,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处于中坚力量。他比我早半年从内长山要塞区宣传处调到组织部党务处。由于他在要塞区宣传处时就写出过多篇很有影响的重磅新闻,调到部里工作不久,便成了撰写文字材料高手和快手,每年都有重头文章见诸报刊;其二,按年龄,他刚满32周岁,正是风华正茂、能够出力的好年华。其三,按职务,他正营职尚不满三年。如果稍缓一下,任满三年,翌年上半年或年底,顺调就能解决副团。于是,我建议他“找一找”,至少应向上级反映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
劝他“找一找”,我认为也是正当的。他家是苏北农村的。婚后,爱人和孩子一直在老家。对这种情况,组织上往往会考虑予以照顾。另外,还有一个小秘密:组织部的朱克部长是江苏人,副部长张钰忠是从内长山要塞区出来的。尽管,那个时候部队风气很正,不讲找门子拉关系,但人熟是实情,加上他的情况特殊,人情加实情,相信组织上是会考虑的。即使要走,至少也要再待一年,调了副团职务再走。
可他告诉我,这次组织安排转业,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我问他为何会有如此冲动?他说,这不是冲动,而是经过了认真考虑后的选择。百万裁军,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要说困难,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谁都能找出一两个留的理由。但是,明摆着的情况是,党务处作为部里的大处(人员较多),至少要走一人。从处里的情况看,老处长刚提升,副处长接任,你职务正连年龄最小,孙干事刚从南京上学回来,你们三人都不符合安排转业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只有我和赵干事,赵干事两个孩子,家在河南农村,家属随军后在家属工厂上班,加上正营职比我早半年,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可以调副团。相比之下,设身处地,组织理应安排我转业。与其要组织动员走,不如我个人先提出来。那首歌儿不是这样唱的吗?“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我个人认为,这句歌词不是一个大道理,而是作为战士必须的忠诚和服从意识。
话不在多,而在于在理。话中没有什么大道理,实际上却包含了一个军人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所必须承载的担当。1987年4月4日,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全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副总参谋长徐信代表全军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凝结着100万将士集体担当的答卷:“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百万大裁军以其辉煌的战果,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华丽转身的大军里,有着我敬爱的老战友难忘的身影。
转眼30年过去。“我的老班长,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回答这句歌词,固然一言难尽,但百度“任全良”,它会告诉你:他转业到地方后,历任沭阳县广播局副局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等职务,现为宿迁市作协副主席,著有杂文集、诗集、散文集,作品获省以上各类奖项60多次。或许,在崇尚“官本位”的人眼里,一个地区的作协副主席算不得什么,那些什么大奖、小奖也动静不大,但在以“诗言志,文载道”而自珍的人眼里,这可是一种足量的修为和境界。正从这个意义上,我的老战友又一次书写了骄人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