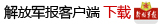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牧师)受宋庆龄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五条意见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同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这时,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
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仍集聚重兵企图“围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但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进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发展,英国、美国同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对于中日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而交由外交部长张群办理,并且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蒋介石不放弃同日本谈判,固然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日本毕竟没有能从这个谈判中得到任何它想要得到的东西。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也被搁延下来。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产党员与之联系订立抗日救国协定问题;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抗日救国的建议。6月初,两广事变的发动者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于9月下台。李宗仁、白崇禧继续与南京对抗,其后由于蒋介石同意桂方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动。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7月10日,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个讲话比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已有所前进。
从1936年8月初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对于他“孤军抗日,迭获胜利”表示祝贺和声援。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如果继续那样做,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国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内某些派系利用抗日的旗帜来反对他的统治,他和广大人民的对立也将会越来越尖锐。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几年来对日的妥协政策。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虽然仍坚持“剿灭”的政策,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政府很快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即: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
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当前全国全民族沦亡惨祸的绝大危险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信中承认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和平的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也坦率地指出,蒋介石的这种解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还是认为现在尚未到最后关头,因而“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
这封信说明,中国共产党确认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指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信中郑重申明:“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信中表示:我们“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信发出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信,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决议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决议也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澈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
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提醒全党,为了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为此,必须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绝不应放松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批评和斗争。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吸收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否则,不能推动与逼迫其上层分子和当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则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