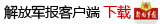星火,星火,你在哪里闪烁?老照片上的战士,你是走向战场,还是撤出战斗?你是在追击,还是在转战?这一切已不得而知,永远湮没在历史的烟云里。只有胶片上当年瞬间显影的感光颗粒,如今依然清晰。
“真想不到,我们的军队当年会是这样!”当我端着手机,把这幅照片拿给今天的年轻战士看时,他们不约而同睁大了眼睛,眸子里写满惊叹号。在他们想来,红军再不济也应该有一身灰军装、有一顶八角帽啊。谁能想到,没有!一切都没有!
照片不会说谎,历史本是这样。形成燎原之势的星火,当年就是这般微弱。
这颗星火,点亮我的记忆。当年采访金一南教授,连续3天的对话中,他闭口不谈他的家世。但我从侧面了解到,他是开国将领的儿子、红军战士的后代。后来,我凭借只言片语在互联网上钩沉索隐,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金如柏将军。

金如柏与郑织文夫妇
按常理说,作为儿子,金一南该对父亲的故事非常熟悉。谁知,他也有一个“没想到”的巨大疑问。1983年,金如柏将军去世前一年。病房里,金一南生平第一次给父亲洗脚,那双脚板让他呆住了。一块块老皮,洗起来硌手。他想不到,父亲这样的干部,进出办公室有地毯,上下班有红旗车,脚板怎么如此粗糙?
父亲的回答,让金一南心潮难平。“他告诉我,红军长征时,有一段时间连草鞋都没得穿,脚板上磨出厚厚一层老茧。行军下来,抬脚一看,厚茧中又嵌进许多沙砾、尖刺。刚开始还往外抠一抠,时间一长也顾不上了。最困难的一段是被分配到机枪连,不但要光脚行军,还要扛沉重的马克沁重机枪,走小路或爬无路的山。直到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二军团的同志才给了双草鞋穿。”
那天,金一南一面给父亲洗脚,一面抬起头惊讶地望着父亲。“该怎样把当年那个赤脚行军、赤脚冲锋、赤脚扛马克沁重机枪的父亲,那个闯过围追堵截、走过万水千山的父亲,与眼前这个拄着拐杖才能走路的父亲相对照?”
父亲,只是当年千万颗星火中的一颗。这颗星火遭遇的风吹雨打,那一代军人都经历过。在漫长的暗夜里,有的星火熄灭了,有的星火黯淡了,有的在风暴中奄奄一息,几乎成为余烬,最终又倔强地燃起。
星火幸存,犹如大浪淘沙。对待很多事情,那一代军人有自己的准则,就像行星坚信自己的轨道。金一南永远忘不了,入伍第一年,因为表现突出,领导决定让他提前提干。他写信报喜,不料父亲的回信异常干脆:“立即返回部队,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金一南感慨:“父亲那代人就是这样,他不是把你提起来,而是把你摁下去。”
星火燎原,要靠自己来燃烧。它的燃料,一定不是狂风中飞舞的蓬草,而是紧贴大地的植被。今天,当我面对这张照片,我不知道金如柏将军是否走在这支队伍里。但当我面对金一南,我却能读懂两代军人信仰理想薪火传承的内涵。
我明白了,他手术后为什么依然坚持趴在床上写《狂飙歌》,明白了他为什么在剧烈摇撼的海军军舰船舱里,冒着惊涛骇浪,修改他的《苦难辉煌》。我想,当他在属于他的战场上冲锋时,当他透过战舰的舷窗,望着那一排排席天卷地的海浪时,一定看到了父辈前赴后继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