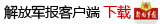交往既久,笔者才意识到这份重要的史料何以过去从来不曾为社会所知。原来,陈明仁虽然曾写有日记,但生前从未向家人之外的任何人提及,更未想过要将它付诸公众。这完全是将军写给自己、留给家人的一份私人记录,其中虽然记述了平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但同时也有大量个人内心自省及家庭琐事的记录。稍微翻看几页,就知道它与那种日记主人预料所写内容可能公开而带有“表演”痕迹的日记完全不同。
这样的日记,才是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最纯粹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这里,可以与徐永昌日记、黄杰日记做一个比较:徐、黄日记中,均有参谋人员协助记录的“起居注”般的个人“行状”,并且抄录了大量主人所经手的军事情报、作战文电等档案文献。这固然为私家记录增加了史料价值,但可以想见这样的记录也是预备好将来与公众分享的,所以日记中个人私情流露甚少,对某些人事臧否时的回避与掩饰比比皆是。而在陈明仁日记中,完全没有“助手”参与,因在戎马倥偬中时间紧张而笔墨俭省,但个人之喜怒哀乐均率性付诸笔端,完全不顾忌日记中的个人“形象”问题。
最初,陈湘生先生仅想提供日记中的滇西部分,帮助笔者完成龙陵会战的写作。在使用这份“未刊日记”完成了作品后,笔者的心愿自然是获得了满足。但是笔者的写作主要聚焦于重大作战行动这条主线上面,文中仅涉及了日记内容中极少的篇幅,且很大程度是以之与军方战报做“互参”“印证”,因此读者几乎不能从中领略这份日记精华之万一。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基于一种学术责任感,笔者向陈湘生先生提出,是否同意将这份日记出版,因笔者供职于解放军出版社,恰好正是出版这类将帅日记的权威机构。
陈湘生先生闻听后颇感意外,因为这想法从来不曾在他心里考虑过。于是笔者费了些口舌,向他絮叨出版这份日记的历史价值:“有这样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存世,我若遇到后保持沉默,是我作为学者的责任,您若坚持把它留在家里不愿公开,则可能成为您的遗憾。”实际上,我这番话是多余的。原本拿出这份日记提供给我,就完全基于陈家人的主导——他们甚至为此专门开了八个孙辈后人的家庭会议商议此事,并报告了仍健在的一位伯父。他们比谁都明白——陈明仁是他们的亲人,更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而现在,确有必要让这份“雪藏”已久的珍贵历史文献公之于众了。

陈明仁(中)与长子陈扬钊(右)、次子陈扬铨(左)
在与陈湘生先生及其兄弟姐妹接触的过程中,笔者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陈明仁的基因和性格,在他的后人身上烙印太深刻了,他们不断使我琢磨着时下被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念叨的“家风”一词。“上将陈府”家风如何,读者可在本书后记中陈湘生回忆祖父的文字中具体感受。笔者的感受是,这份家风在昔日可能不算新鲜,但可能只有陈家后人把它毫不走样地保持到了今天,似乎没有经过一丁点岁月的销蚀。比如,时下人们早已习惯了“官二代”“红二代”亲自为父辈张罗影视剧或传记、文集、座谈会之类,你能想象开国上将的后人却在犹豫是否同意将他的战时日记付诸出版吗?
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作为“战犯”在功德林改造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因为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文史资料撰写工作,反而留下了很多记述个人功绩的文章;而高举义旗反对内战守护了和平的陈明仁将军,反倒没有留下一篇回忆其抗战功绩的文章。在日记里反思检讨自己的缺失和不足,几乎是陈明仁写日记的主要目的之一。他本是个极为率真的性情中人,但在肩负重责、宦海沉浮、人际炎凉、生计困顿的战争时期,他不得不与自己的真性情“拧巴”着来——日记中反复警示自己戒赌、戒酒、戒怒、戒多言……慎独慎微、严以律己如此,自然从骨子里反感自我吹嘘。即便是在滇西战场这一堪称辉煌胜利的战役中,他的笔下也大多数是对仗没能打得更好、部队素质不如人意的批评和自责。在其个人指挥作战的华彩乐章——畹町回龙山之战胜利后,他在日记中最自豪的一笔不过是:“今日之胜利,争得莫大之面子,官兵殊能用命,欣慰之至。”纵观其全部日记,他对个人战功的自我评价,没有超过这一句的。而对后来在内战战场上让林彪大吃苦头、为他人津津称道的“四平大捷”,他却数次以“惨象目不忍睹”“不胜感慨系之”来忏悔。
在陈明仁的性格谱系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敢于“抗上”,湖南人的“骡子”精神在他身上极为鲜明。他会经常坦率地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而负责,但对认准的道理却没有过“畏惧”二字。坊间传说,1942年3月在昆明,陈明仁因为不服蒋介石批评其部队官兵“服装破烂”,抗辩“服装只发四成,当然破烂。其他部队皆然,不仅本师也”,并于激愤中撕掉中将领章扬言“这个中将不当了”。日记证实,这件事并非妄传,陈明仁本人是这样记述的:“(三月四日)三时半晋谒,不数语即引起委座大发雷霆。余亦以此事太遭不白之冤,恃爱妄言,说明服装破烂,余不能负责。当时态度言辞不免过剧,致被收押,责令宪兵十三团于明日送往重庆。余以无罪,心甚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