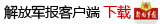资料图
敌机飞走后,他才艰难挣扎着爬到不远处的水田灭火。我们赶到抢救时,见他头发全烧焦了,身上黑一块紫一块,严重烧伤,隆起好多血泡,已昏倒在地。我和卢姐给他包扎后,让担架员火速送到救护所。所长亲自接诊抢救,首先打了抗休克的止痛针,清洗烧伤创面。
这时,王教员苏醒过来,只见他艰难地睁了睁眼,说:“水!”我立即打开水壶盖,可因他头部烧伤,张嘴困难,怎么喂水呢?机灵的卢姐说:“小侯,快去房东阿妈妮家后院剪根芦苇管。”我拔腿跑去剪来芦苇管,给他喂了水。王教员眼睛微闭,嘴唇嚅动了几下,断断续续地说:“口袋里……有封信……还有一枚纪念章,寄……”话没说完,他便停止了呼吸。

清理他的遗物时,我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沾血的信,这封未寄出的信是写给安东市第六中学姜淑香同学的回信,正是那封写给学员的示范信。因战地没法邮寄,卢姐让我保存好,待有机会一定完成烈士的遗愿。
事后,我们将王教员安葬在地镜洞山坡上的大松树下,卢姐在一块木板上工整地写了“志愿军文化教员王俊杰之墓”。一颗热情赤诚的志愿军军人的灵魂,在此永远安息。
此后,我再也见不到战友王教员的音容笑貌,听不到他洪亮的教书声。但他在弥留之际托付的这封信一直与我朝夕相处。行军时,装在挂包里与我同行;夜宿时,放在枕包里与我共眠。
那个冬夜,我们救护所驻地大乌里山沟遭敌机轰炸,三班防空洞被炸塌。战友们摸黑刨土石抢救受伤的同志,寻找被埋的物品。我急于寻找存放信的枕包,忍痛扒拉着土石,手被磨破了,指尖滴着血,终于在天亮时扒出我的枕包,找到了那封信。
1953年7月27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凯旋,驻防鸭绿江边沈安线(现沈丹线),我们军医院驻在凤凰山下吴家崴子。刚回国,中央歌舞团、京剧团即来慰问演出。大家兴高采烈地要到城里看节目。卢姐对我说:“小侯,咱请假送信去。”于是,我与卢姐一起来到了所部。
没等开口,所长问:“你俩来有啥事?”
“我们请假,到安东跑一趟,把烈士王教员的信送出去。”所长知道这封信的来龙去脉,毫不犹豫地同意我们去办。
我们从来没坐过客车,记得入朝到安东,第一次坐火车坐的是闷罐货车。这次打听着坐上了从凤凰城站去安东的客车,过了三个小站,就到安东站了。下车后看见站台上都是欢迎的学生们,他们手持鲜花,打着“热烈欢迎志愿军凯旋归国”的横幅。我俩急忙问有没有六中的学生,结果没有找到,只好出站沿街问路,终于问到第六中学所在地。
一进校门,正赶上老师集合学生队伍,分批到车站迎接志愿军归国。老师和学生们见我俩是志愿军,很热情地围了过来。我们打听姜淑香同学时,老师说她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今天没来,但初一一班的姜淑英是她妹妹。稍后,老师叫来了齐耳短发的姜淑英。我想把信交给她,卢姐说:“不,一定要亲自交给姜淑香,这是王教员的重托。”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小姑娘向老师告假,蹦蹦跳跳地领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走进了一个清静的农家小院。
院内,一位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正在一棵山楂树下的石台上写着什么。妹妹喊了一声:“姐,志愿军叔叔阿姨看你来了。”小姑娘站了起来,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我们两个陌生人。卢姐走近眉清目秀的小姑娘,说:“你就是姜淑香啊,可算找到你了。我们是刚从朝鲜前线归国的志愿军,今天给你送来一封信和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这封信是志愿军文化教员王俊杰叔叔写给你的,纪念章也是他送的。他刚写完信不久,就在一次敌机空袭时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