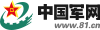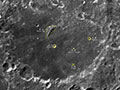能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奉献一生,他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中国航天大事记里有这样一个瞬间——2012年6月29日10时03分,神舟九号返航,在太空中遨游了13天的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随返回舱着陆。
那一刻,在距离着陆点四王子旗500多公里的北京市中国航天科技大厦里,一块电视屏幕正直播着现场画面,屏幕前的梁思礼倚靠着座椅,紧皱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
遥想当年,新中国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归国后的梁思礼面临着极为窘迫的局面:没有资料,没有仪器,没有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但他知道“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学自动化出身的梁思礼挑起了担子,成为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风华正茂的他,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人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他曾坦言,“感到无比的光荣与自豪”。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的经验要比成功的经验宝贵得多。“东风一号”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也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具有深远意义。然而,梁思礼谈及“东风一号”的成功时,总是简单带过。1962年“东风二号”发射试验失败却被梁思礼屡屡提及,那次导弹发射不久后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炸出了一个大坑。
望着远处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很多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从第一次试射起,一个又一个十年,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
可“摔”得越痛,父亲梁启超的话便越发透彻真切:“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人类心理的知情意,其发达圆满的状态就是“智仁勇”,即如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人要想成事,须得有遇事能断的智慧,一不忧成败,二不忧得失。
况且,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经历过无数次失败,才有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科学家的每一丝获得,都像是在废墟里等待萌芽。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第一”,都是在一次次失败中孕育成功,在艰难探索中走向胜利。
上世纪80年代初,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计算机软件的作用愈加凸显。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退居二线并未远离“战场”,他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航天人
退居二线后,梁思礼并未远离“战场”,而是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他喜欢的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从2006年到2012年7月,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梁思礼所在的中国老教授协会,面向全国高校开设了《当代中国国情与青年历史责任》课程。6年时间里,梁思礼以《中国航天精神和素质教育》为题,先后为北京十几所著名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直接听众3400多人,全国网络视频听众有57000多人。
面对台下的年轻人,梁思礼曾经多次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求学时,他有位好朋友,这位朋友后来留在了美国。几十年后,这位朋友成为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为航天工业部的总工程师。
朋友的年薪在上世纪80年代是几十万美元,住着高级别墅。有人问梁思礼内心的感受。梁思礼说:“如果我当年留在美国,不会比我这位朋友差多少,但我是为了我的祖国而离开的,我感到自豪。”
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年也是梁思礼回国50周年。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威风八面的导弹武器从眼前经过,回忆起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梁思礼感慨万千。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在梁思礼家人的回忆里,梁思礼晚年仍关心国家大事,“经常与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老校友见面,谈论国内外大事”。他除了虚心听取众人议论,也常常谈及有关导弹的问题。
有趣,是父亲留给他的人生锦囊。“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受父亲的影响,梁思礼的兴趣非常广泛。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旋律欢快的曲调。旋律响起,躺在病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都会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音乐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最后的希望被他写进遗嘱。追悼会上,梁思礼生前爱听的《圣桑小提琴协奏曲》被循环播放。与梁思礼共事的“长征二号F”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二人相识半个世纪,送别老同事时,77岁的刘竹生颤抖地写下一句话:“下辈子我们还一起搞航天。”
普渡大学埋首实验、国防部五院日夜鏖战、酒泉发射中心发射前检查、站在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领奖台上……在每一个人生节点,梁思礼和其他“驯火者”一样,被镌刻在历史的坐标上。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也许总有东西比死亡更久远。”梁思礼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走了。而他对祖国的热忱,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及对生命的“兴致”与“乐趣”,却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