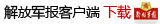爱因斯坦说,通向人类真正的伟大境界的通道只有一条苦难之路。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攀登“高峰”的道路异常崎岖,苦心经营、孤诣打磨是创作者登顶的金科玉律,也是文艺“高峰”矗立的必然选择。
文艺百花园里“高峰”峥嵘,而每一座“高峰”缔造者的诉说都蕴含着一个“苦”字。福楼拜有一封信札写他著书的艰难:“我今天弄得头昏脑晕,灰心丧气。我写了四个钟头,没有写出一句来……今天整天没有写成一行,这工作真难!艺术啊,你是什么恶魔?为什么要这样咀嚼我们的心血?”“苦”字伴随创作者的一生和每一部作品,新人骁将,概莫能外。路遥曾说:“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苦”是艺术之梯,托举着攀登者拾阶走向创作的春天;“苦”也是艺术的“九垒之土”,天长日久堆积成“高峰”。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欲登“高峰”,当有无论顺境逆境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坚忍不拔之志。1953年,著名作家柳青为一颗文学初心毅然辞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职务,定居皇甫村,用“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的信念,天天在田间地头转,为世人留下了史诗般巨著《创业史》;作家陈忠实在著作等身、好评如潮之时,决然回到落寞多年的祖屋,以写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的宏志潜心创作,用恒久的初心蘸着所有书写者的“苦”,写就了令人荡气回肠的《白鹿原》。“意为心之足,防意不严,走尽邪蹊。”面对艺术之外的诱惑,定力不坚,终是随波逐流,徘徊于艺术的“稳境”甚至“疵境”,难进“化境”与“醇境”。
文艺“高峰”来自经年累月的捶击敲打和风雨雷电的修炼,急不出来,炒不出来,图热闹更是难成。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相继发表后,各种宴请、采访、签名纷至沓来。有一天,他把佣人叫来:“从今天起,我死了,就死在我的房间里,不过别忘了给我送饭。”9年后,世界文学史上的皇皇巨著《复活》脱稿,托尔斯泰也同时复活。托尔斯泰的一死一活形象地告诉我们,要成就一番伟业,必须给自己准备一条冷板凳。音乐大师贝多芬坐“冷板凳”的功夫也不浅,他成名后为了躲避造访者,在维也纳居住期间共搬了79次家,目的正是为了让自己坐“冷板凳”。“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每一部时代大作都透着大家的艺术良心和守静之道。
国学大师钱穆说:“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诀窍无他,都是能人肯下笨劲。”路遥在谈及《平凡的世界》创作时说:“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工作量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而有些作家之所以难成气候,原因恰如胡适所言:“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必经三种境界”。只要我们躬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信念,定能蓦然回首,“高峰”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