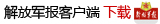李君放抱起老兵刘梦元。王天文摄
2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他们一次次从死神的指缝间艰难爬出,相比那些牺牲在战火中的战友们,他们觉得幸运、充满感恩。
我和李君放曾交流过采访老兵的感受——对我们而言,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这些幸存下来的老兵对生活没有丝毫的抱怨,他们一次次从死神的指缝间艰难爬出,相比那些牺牲在战火中的战友们,他们觉得幸运、充满感恩。平山团的司号手“喇叭爷”,晚年用在温塘集市上吹冲锋号的方式为贫困大学生筹集学费。大吾川里朱坊村的卢献寿,15岁参加平山团,4次立功,8次受奖。带着伤病南归后,他回乡当农民,日子过得贫苦,可每月交党费都决不延误……
我们用镜头和文字,记录着这些老兵们的晚年生活。
2012年一个极冷的冬日,我和李君放准备去采访两个平山团的老兵。他前段时间刚发现,我们正要采访的王冠章老人是平山团的第一批战士。我们的车翻过一个坡岭转入乡间小路,向南庄村开去。忽然,一支送葬的队伍出现在眼前,白色的孝帽、彩色的花圈在冬日苍黄的山岭上十分显眼。我心里一紧:“该不会是王冠章老人去世了吧?”但李君放说一个多月前还给他拍过照片,那时老人身体还挺硬朗,应该不会吧。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到了王冠章老人家,门厅前白纸黑字的七单(一种记录死者祭奠日期的纸条)赫然出现在眼前,老人刚刚去世!遗憾笼罩了我的内心:又晚了一步。我们只好采访了他的儿子。在儿子眼中,父亲不是一名军人,而是一个郎中。老人因病退伍后,几十年如一日在村里行医。村里人不太了解他的戎马生涯,只知道他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好大夫。过年过节有人生病,他也一样出诊,甚至曾连续守在病人身边几天几夜。关于平山团的事,他的儿子所知甚少,只听父亲说起过,带他们打仗的旅长王震记性特别好,头一天看战士们站队点名,第二天碰面就能叫上他们的名字。
天近正午,我们告别南庄,简单吃过饭后直奔十多公里外的霍南庄村。李君放说:“下午咱们一定能采访到刘增英老人,因为20天前我为老人拍照时他还能自己走到院里呢!”
轻车熟路,他把车直接开到刘增英家门前。我们兴奋地推门入院,我大声喊:“有人吗?”一转身,李君放已愣在那里,他黯然一指:“看那里的七单!”原来,刘增英老人已经去世半个月。
类似的情况李君放经历过很多次,他开始拍摄平山抗战老兵时,健在的老兵大约有300多人,过了两年就去世过半,数年下来,已零落无几。这些生活在农村的老兵大都90多岁了,常常是李君放前脚拍完照,老人后脚就去世了。好在,他辛苦奔波,给这些老兵留下了人生最后的影像。
我们在刘增英家的院子里转了转,发现屋门没锁就径自推门进去,在屋里发现了他失明的老伴。老人说起刘增英当兵打仗的事儿,不禁频频落泪。原来,刘增英是孤儿,7岁给人家当小长工,12岁时赶上平山团征兵,就跑去跟姥姥说:“我去当兵吧,打鬼子,能吃饱饭。”
刘增英后来成为平山团的司号员,在战场上多次负伤。平山团南下时,他因伤回到家乡,拄着拐杖当起了农民,村里所有的义务劳动他都参加,辛苦生活了一辈子。近几年他有些糊涂了,但当提到牺牲的战友,特别是在南下途中牺牲的平山团团长陈宗尧时,他都会流下泪水。
刘增英的老伴在床上哭着讲述他的一生,我在床边流泪记录着。李君放在一旁拍下了我们相对垂泪的照片。
那以后,刘增英的老伴也被李君放列入他时常看望的老人名单。在李君放的拍摄手记里,我看到这样的文字:“2013年8月11日,和好友郭勇去看望已故老兵刘增英的老伴,我们到后得知老人已在8月4日过世。人已去,房已空。愿老兵和他的老伴在地下相见!”叹惋之余,李君放拍下了那把放在窗前的空椅子,老兵生前常坐在这把椅子上。这张照片,后来成了李君放《平山老兵》摄影作品集的封面。
李君放拍摄老兵的这几年,一次次去看望这些老兵,不仅在精神上给他们慰藉,过年过节还为他们送去米、面、油,或者递上一些钱。他有时还赶去参加老兵的葬礼,为老兵抬棺,拍摄老兵下葬的仪式和纸花飘零的坟头。他的照片感染了许多人,带动了更多志愿者关注老兵、关爱老兵。
记得一天深夜,微信群里的一位友人发了一组照片,是李君放和他们一起去看望刘梦元老人时拍的。老人病重,已瘫痪在床。那天天气很好,李君放轻轻抱起老人去院里晒太阳。羸弱不堪的老人,婴儿般依在李君放怀里……我盯着那张照片,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