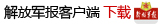我如实相告。
此后我们就没再交谈,只是并肩走着。在科伊索尔山顶时,我们见到了积雪。就像在南方常见的那样,太阳一落山夜晚就随即来临,好在积雪映出的光亮能使我们轻易地看到前方的路——虽然仍旧依着山势蜿蜒而上,但不似以往那么陡峭。
我把行李箱重新放回到马车上,那些公牛也换成了几匹马。我最后一次转身望向山谷深处,从峡谷涌出的滚滚暮霭早已把它完全覆盖,山谷底一丝声响也没有。那些奥赛梯人把我层层围住,吵闹着索要酒钱,遭到了上尉严厉地斥责后立即四散开去。
“哎,这帮人啊!”他说,“他们从前并不知道俄语里‘面包’怎么说,可是他们学会说‘长官,给点儿买酒钱吧’。咳,我宁可雇些鞑靼人——至少他们滴酒不沾。”
离驿站还有一英里的路程,四周一片寂静,甚至从小虫子发出的嗡嗡声就能得知它们往什么方向飞。左边是漆黑的沟壑,放眼望去,群峰迭起,深蓝色的山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在黄昏最后一抹余晖的映照下,矗立在白茫茫的天际。夜幕下群星闪耀,我颇感奇怪,这里的星宿与北方家乡的相比似乎显得更高更远。山路两旁随处可见赤裸裸的黑褐色岩石,偶尔还能看到探出积雪的枝权,然而竞没有一片枯叶随风摇曳。在这片死寂中,疲倦的驿马那沉重的鼻息声,夹杂着马具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叮当声,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愉悦。
“明天天气准不错。”我说。
上尉什么话也没说,伸手指向我们正前方的一座高山。
“那是什么?”我问道。
“古德山。”
“噢,是的,怎么了?”
“您看看,它正在冒烟呢。”
古德山的确是在冒烟。一圈圈的轻烟萦绕在它四周,山顶上漂浮着一块乌云,在山峰的阴影衬托下显得如此黑,宛如是夜空中的一块墨迹。
驿站和它周围石头屋子的轮廓依稀可辨,远方——点点灯光闪烁似乎是在迎接我们的到来。此刻吹来一股潮湿的空气,峡谷中传来轰隆隆的声响,随后细雨飘零。我还没来得及披好斗篷暴风雪就袭来了,我不禁满怀敬畏地望了上尉一眼。
“我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他烦躁地说,“谁也没办法在这样的暴风雪天气里翻过这些山岭。”
“喂!”他冲车夫喊道,“十字架山这儿以往有过雪崩吗?”
“没有,长官,”奥赛梯车夫答道,“但是下过无数次大雪。”驿站没有为过路人提供客房,所以我们不得不待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石头屋子里。我邀请上尉同我一起喝杯茶,幸好我带着铁茶壶——这也算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的一种慰藉了。
石头房子的一侧依山而建,门前有三级又湿又滑的台阶。我摸索着进了屋,撞上了一头母牛(在这些地方牲口棚占据了仆人房间的过道),接着羊咩咩地叫,狗也跟着吠了起来,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幸好有一侧闪着微弱的光,借着这光线我找到了另一个类似门的通道。映入眼帘的一幕令我颇感有趣。屋子中央的空地上有一个火堆,噼啪作响,冒着浓烟,这些烟又被风从屋顶缺口处倒灌进屋子里,弥漫在房间上方,以至于我费了好大工夫儿才适应。石屋里,两位老妇人和一大群孩子坐在火堆旁,还有一位瘦削的格鲁吉亚人,所有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也在火堆旁点燃烟斗,抽起烟来。不久,茶壶就欢快地吹起了哨子。
“真是一群可怜的人啊。”我指着那些脏兮兮的招待员说。这些招待员正漠然地望着我们,一声不响。
“这群人打从娘胎出来就是群笨蛋!”他回答道,“信不信由你,他们全都一无是处,什么也学不会。就拿卡巴尔达人和车臣人来说吧,或许他们是强盗,是穷光蛋,但他们的确英勇无比,敢做敢为。唉,这群人对武器毫无兴趣,从来没见过他们谁身上有把好匕首。这就是奥赛梯人。”
“您在车臣待了很久吗?”
“我和我的伙伴在那里的要塞待了十来年,靠近卡敏尼勃罗德。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听说过。”
“唉,那群混蛋可真让我们头痛了好一阵子!谢天谢地他们现在可老实些了。你一旦走出要塞围墙一百码远,就会有一帮野蛮人守在那儿,他们个个身手敏捷,一眨眼的工夫,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绳索一套上脖子,子弹就打穿了头。”
“想必您一定听过很多奇闻趣事吧?”我好奇地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