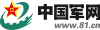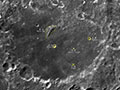王毅:田华老师,您好!因为这首我为人民军队92年峥嵘岁月,新中国70华诞创作的诗歌《前进,英雄中国》而与您相识并交流,深感荣幸。您作为朗诵者,对这首诗的感受如何?
田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2周年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我与吴俊全、温玉娟、杨帆三位战友一起,在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郭思达创作的音乐伴奏下,由著名指挥家张海峰现场指挥,朗诵了这首诗歌。现场震耳欲聋的掌声,说明了观众无不被感动、感染。这掌声是为人民军队而鼓,为新时代而鼓。诗中这一句:“从此,中国拥有了崭新的精神高度/审美的火焰如同穿透云翳/与太阳融为一体/铺展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仅仅用了七十个春秋/就让千年古国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朗读起来特别喜悦、豪迈。
当我朗诵到“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我就有要流泪的感觉,“七十年,沧桑一瞬/可是又那么崎岖漫长/猎猎飘扬的旗帜/迎击过多少雨雪风霜”。她让我想起电影《党的女儿》,想起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的优秀儿女。全诗节奏分明,声情并茂、激越铿锵,具有长久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有英雄情结的人,才能创作出这么感人的诗歌。
王毅:感谢您的夸奖。你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当时是什么动力驱使?当年又是怎样的情况?
田华:我从一个12岁的农村小姑娘成长为一名军人,一位军旅老艺术工作者,我要感谢党和军队的培养,感谢军队电影事业的发展,感谢八一电影制片厂。我出生在河北省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儿时的记忆大都是亲人被日本鬼子残害的场景。我的二哥在区里工作,在一场鬼子的“扫荡”中牺牲;我的三哥于1937年在聂荣臻部来河北时参了军,第二年也牺牲在了冀东的一场战役里,他们都是千千万万普通乃至无名烈士的一分子。我大伯被烧死在红薯窖里,大姐被一边喊“花姑娘”一边追赶的鬼子吓疯了,我父亲则是被敌人抓去后最终病倒身亡。这一切对我的人生影响巨大。我在12岁的时候报名参加抗敌剧社,成为儿童舞蹈队的一员,开始接受党和军队的培养,我的名字田华就是汪洋副社长替我改的。
王毅:当年八路军的生活怎样?你们当年慰问英雄官兵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田华:当时剧社活动特别多,慰问战士、群众宣传、驻地教歌、开办识字班等等,给我提供了很多学习进步的机会。记得第一次正式演出是慰问参加“百团大战”的革命队伍,在一个舞蹈的最后,我爬上梯子向凯旋的抗日官兵敬礼,直到最后一个士兵通过,胳膊都举酸了,但是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骄傲,因为这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个正式角色。从那以后,我参加了剧社创作的《子弟兵和老百姓》《红枪会》、歌曲《让地雷活起来》等文艺节目的表演,还经过“无人区”到山西敌后炮楼下的农村去演出,历经炮火的锤炼。
16岁那年,我入了党,在面向党旗宣誓时就决心一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部队打到哪里,我就跟随着抗敌剧社演到哪里。从保定、石家庄到天津,再到张家口、宣化、北京,为部队官兵演,为驻地群众演,还曾在张家口为苏联红军演出。
王毅:今天十二三岁的孩子,都还在妈妈怀里撒娇,真难以想象您当年的坚强。
田华:1940年初,我刚参军时,年纪比较小,不适应,去了一个星期就开始哭。后来人家说,你老是哭,就不进步了。这么说对我起的作用很大,我暗下决心,我得抗日,我得坚强,得好好学习、好好进步。从那以后,我严格要求自己,早上一听见哨子声,就赶紧穿衣、叠被、打背包,然后到院子抢扫帚,扫完院子赶紧跑去沙滩练功,回来以后洗漱、吃饭,吃完饭马上又吹哨子,若是敌人没来,我们就排练、演出。平时工作、生活,有困难都是抢着上,见了荣誉就让。
当时我们都是住老百姓的房子,有火炕的房子老百姓住,我们住没有窗户和门的柴火房。冬天,我就先抢有风的地方,哪里冷住哪里。到了夏天,就抢不通风的犄角旮旯。真不是为了表现什么的,而是自己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因为党员同志都是这么做的。这与现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上面起了一个好头,作出榜样,然后把整个党风和社会风气带好了。
我始终要求自己不仅要做一名好演员,更要做一名好党员,要像当年牺牲的战友和英雄模范一样,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组织,管住自己。那时候安排演出,叫我演就演,不叫演就不演,叫演什么就演什么。什么名啊、利啊,从来没有考虑过。
1943年,敌人的第三次“大扫荡”实行更加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演出队的小战士们大多数都去了延安,只有我和三个战友留下。我们急得直哭,一心想跟随战友们到毛主席身边去,但是根据任务需要,我们继续留在晋察冀根据地与敌人战斗。我们晚上演出,白天睡一会儿,依靠演出提振根据地的军心、民心,同时进行抗战宣传实践,就是“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