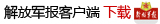全县动员的修路之役
今天,询问几乎每一个漾濞的九旬老人,都有参与修建滇缅公路的经历;任何一个漾濞本地人,家里几乎都有修过路的亲属。
“从天生桥到顺濞河,沿线布满窝棚,全是民夫,从老人、妇女到八九岁的娃娃都有,‘妇女扶炮杆,男人打铁锤’。”幸存的修路民夫告诉记者。
今年87岁的白春荣当时只有9岁,对修路的艰难记忆犹新:“真是太苦了!睡树叶搭的窝棚,早上六七点起,干到晚上八点才收工。壮劳力们挖山砍树,我年纪小,天天用畚箕背土,每次只能计半个工。”
吃不好、没工钱,修路纯属为抗战出力。89岁的马树华说,民夫每人每天可以有五两米,中午和晚上收工各吃一顿,能果腹就不错了。
在这样的苦日子里,漾濞人硬是从山坡上扒出了一条路,1938年5月即告贯通,比滇缅公路全线贯通早了3个月。
路通之后还要不断修建改造。马树华回忆,为了填补道路上的坑洞,自己和小工友两人每天要抬一立方米石头,工头严到用尺量。两人年纪小,常干到太阳下山都完不成。
尽管修路艰苦,但漾濞人明白它的意义。“都知道是为了打鬼子。路修通了,才能运物资上前线。”马树华等人都说。
随着公路贯通,汽车来了,物资源源不断运至。白春荣至今还能准确回忆起各种车辆:煤炭车、吉普车、GMC十轮大卡车……
修路之际,他们还和盟军结下友谊。“美国盟军会给白砂糖吃,我就竖起大拇指说‘顶好’。”白春荣说。他至今还记得盟军教他的英文单词,能顺溜地从“one(1)”数到“te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