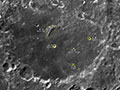三、练拳脚,操缨枪,舞刀弄棍演兵场
1929年五六月间,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岽下欧屋练武场上却人声鼎沸。
“注意出镖的方向、速度和力度,只有心神合一,目标一致,拳镖贯通,才能在战斗中争取主动。”身材魁梧的欧阳克淇站在十七个欧姓同族兄弟、侄子面前,一边做着示范,一边向他们解说拳术和使镖的要领。
酷暑下,族亲汝万,侄儿可椿、可棋、可森、可琪,族兄弟克沭、克洪、克淳,族侄子可镗等17个青壮汉子跟着口令,一个个都练得汗流浃背。可椿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上过几年学,他深知“文能化人、武能安邦”的道理,所以一方面不断鼓励年轻人习武写字,一方面自己也积极学习各种武术要领。
自从于九里岭遭匪害劫后余生,并带着欧家兄弟们回到家后,欧阳克淇陷入长久的思考之中。
从欧姓祖上入闽挑盐贩盐起,也曾遭到不少匪劫,大多都能化险为夷。欧姓拳法对付几个毛贼绰绰有余,且欧姓贩盐队伍少则十五六个,多时达到二三十个,人多势众,更有拳法护身,刀戟棍棒在南拳下均能化为乌有。但眼下匪徒们的武器发生了变化,刀棍换成了乌铳,又由乌铳换成了洋枪,比起之前的大刀长矛和土枪来,更难对付,九里岭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欧阳克淇面前:今后众兄弟如何再吃挑担这碗苦力饭?
“兄弟们,以往我们欧姓人出门在外凭借一身武艺就能闯天下,但现在不行了,眼下乱世,草寇出没,通往闽赣贩盐的道路又是崎岖的山道,路难行不说,兵匪之患最是可怕。如用老法子挑担挣饭吃,性命难保,我们要有新的计划,寻找新的出路。” 欧阳克淇召集兄弟们,口吻坚定地对大家说。
大家议论纷纷,欧阳克淇内心也很不平静。他忽然想起上次程排长送给自己的两把扎着红缨的梭标。转身他回到房里,从柜子里拿出用红布层层包裹着的梭镖,久久凝视,良久,心中忽然就有了主意。
兵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他决定改变传统单一的靠拳脚走天下的老套路,创造一种新式武器。
于是,他走到正厅,将族亲汝万,族兄弟克沭、克洪,侄子可椿、可棋等17位年轻力壮的汉子召集到跟前,将自己的想法对大家说了出来。
欧阳克淇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出门在外,不光练拳护身,还得有护身家伙。现在的世道已经大变,单靠拳脚会吃亏的,我们要有自己的武器。”
克淇边说边将程排长送给他的梭标拿出来,并顺势将墙角边搁着的木棍也一同拿了过来,说来也巧,那木棍的大小正好能合得上梭镖的端口。配上五尺来长的杂木棍,克淇刷刷一挥舞,木棍与梭镖俨然成了一把杀人于无形的“长枪”。不仅如此,克淇还将包裹梭镖的红布系在“长枪”的连接处,把众人的眼睛一下就点亮了。
大伙议论纷纷。
“叔,梭标就梭标呗,干嘛还系个红绸布?”可森不解地问。
“好看呗。”
“不仅好看,我觉得还有一层深意。”平素与叔关系特好的可椿接话道,似乎只有他能洞悉克淇的心思。
“是吗?”大家面面相觑。
看到大家疑惑的目光,欧阳克淇点头说:“对呀,你们记得救我们的程排长吗,他可是现今让那些土豪地主们一听就恐慌的红军呐!”
“那天你们也听到了他向土匪训话,说土匪是黑道。黑道黑道,另外一面就是红道,不用说,那红军兄弟就是红道啰,也就是阳光大道的意思。他们替穷苦人撑腰,我们就得学上他们。”他深情地抚摸着眼前这把“长枪”,忽然语气铿锵地说:“以后这个长枪,我们就叫它红缨枪。干脆,我们成立一支红缨枪队,全系上红绸带,以示追着红军走,怎样?”
“好呀,好呀,早该有这样一支队伍了!”大家兴奋地响应起来。
“克淇叔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可椿带头大声说道,几乎是同时,十七个本族兄弟、侄子,异口同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对,叔,你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 可森附和道。
“是呀,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全听你的。”汝万面向克淇,也大声地回应克淇的提议。
克淇威信很高,不仅因他侠肝义胆、办事公道,而且他的武功在岽下无人能敌。
记得有一年,大年二十九,全村凑在一起贺岁,有挑事的同伴说:“克淇,你敢不敢赌?”
“赌什么,有什么不敢的!”
“就赌你能否追上狗。”
“狗?”
“对,敢不敢?”
“好,来呀。”
同伴二话不说,将一串鞭炮扎在黑狗尾巴上,点上火,受惊吓的黑狗猛地一激凌,疯一样在村前的空坪上狂奔。
嗖嗖……练家子出身的克淇,一阵风似地追着黑狗往后山窜,引来全村人看热闹。追逐中,黑狗狂吠不止,而克淇却面不红气不喘,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狗拦在身下,那身手让全村人目瞪口呆。
眼下,见大家都附和自己,欧阳克淇心里有数了,便带人来到离岽下村不远的老圩场高围脑铁匠铺,让曾铁匠按照程排长送给他们护身的梭标,一下打了十六把一模一样的。合起来正好是十八把,岽下村梭标队十八条汉子每人一把。
众好汉把它们磨得锋利发亮,学着克淇,将它们配上坚硬的木棍,系上红绸带,一支威风凛凛的红缨枪队就组成了。
几天后,岽下村十八把红缨枪队正式成立,村里举办庆祝大会,全村欧姓老幼都积极地参加了。随后,红缨枪队在村子后山向大家表演了红缨枪枪术,人虽不多,但是已经有模有样,大家情绪高涨。
此后,每当茶余饭后,岽下村红缨枪队一有空闲,便操练武艺。全村二十多户人家没有事的也聚集在场上看后生操练,连几个幼童也拿着长短不一的木棍,一招一式地跟着练了起来。
五月中旬,朱毛率红四军打回到大柏地,还在圩上向群众发放了大洋,弥补上次大柏地战斗给群众造成的损失。此事传到岽下,引起了大家一阵热议,交口称赞共产党的红军是支好部队。
谁知,共产党红军的入境却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恐慌,国民党的人在县乡四处作反共宣传,深恐老百姓会跟着共产党红军走。当得知岽下村有支十八把红缨枪队时,立即干涉,派人到村里宣布说:“此事有聚众造反嫌疑,队伍必须立即解散,红缨枪缴掉充公。”
岽下人一听火了,全村人出来据理力争,说:“我们长年外出行脚、做买卖,常遭土匪抢劫,打几把梭标路上防卫,这难道还犯法么?”
“好呀,你们把梭标缴去,我们也不去挑担了,到你们衙门吃干饭去!”
……
县府官员见众怒难犯,而且民间置有梭标也不犯法,只得灰头土脸地回去了,岽下村十八把红缨枪得以幸存下来。
于是,岽下村人一面继续习武护村,一面沿袭着挑盐行脚的营生,继续替县城的本家商号运盐贩盐,同时也替城里的其它商号挑担贩货。只要商号需要,即早出晚归,跨州过府,晚了就夜宿客栈,晨光微露又挑担上路,以苦力劳辛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