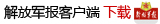李发锁本来计划一年半至两年完成《围困长春》的写作,可写到一年半便写不下去了。他回忆说:“原因是觉得站位低,视角窄,没有用大历史观从二战后世界格局来看国共对东北的争夺;同时,弄不明白围困战的性质和规律。”通过沉淀下来认真思考,李发锁认为:一定要从大历史观去解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如果单单就围困写围困,势必陷入一鳞半爪之泥淖。于是,李发锁将东北解放战争及围困长春战役置于当时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复杂局面中进行考量,把局部战役放到世界大格局之中进行战略与策略剖析叙述。既讲述了我军的战略、策略对战争走向的重要性,又辨析了长春围困战若干似是而非的说法。
在大历史观中透视战争风云,“久困长围”已不再成为问题,那是当时根据敌我双方实际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战争策略。
《围困长春》还破解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在短短3年就被共产党推翻了?”全书几乎都在写国共两党在各方面的比较与角斗。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不容诋毁。叩穿历史以正视听,该作品对于强化党的执政能力,不忘初心、发扬光荣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
李发锁秉持“真实即力量”的创作理念,以档案、史实为依据,用真实还原历史。整部作品脉络清晰,事理透彻,文笔洗练,意蕴悠远,叙事缜密细腻,人物生动鲜活,呈现出现实主义历史创作的大气象。
在《围困长春》创作中,李发锁始终用证据说话,采用了许多国共双方的档案资料,尤其是敌方原始文件(如,郑洞国签发的文件、国民党的原始会议记录等),仅书中标出的重要史实注释就有900多条。其中,相当一部分条目都是采取双证据引用。诚然,作者的笔墨不只是停留在战争的现场,而是深入探究战争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战争走向的影响,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秉笔直书,正本清源,既写胜利与成功,又写失败与挫折。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场,作家善于抓住核心事件与核心线索,对主要人物进行多侧面描写。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上,李发锁认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不矛盾,而真实压倒一切。关于长春围困战,那些似是而非的“真实”,那些无中生有的质疑,那些别有用心的造谣,在《围困长春》的真实书写中一一败下阵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一连串的荣誉足以说明,这是一部饱含历史重量和思想能量的纪实大书。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所说,这是一部“复现东北决战的恢弘力作,体现了作家的史学功底和文学才华,深刻揭示了战争背后各种力量的较量。”
真实不仅是作品生命力的第一要素,而且直接反映了作家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良知。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纪实作品《围困长春》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个深度发掘历史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