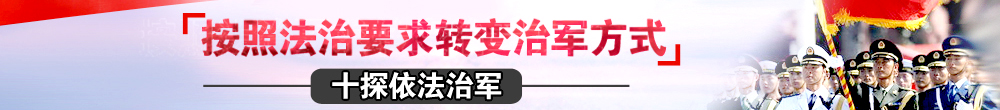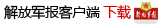“喀秋莎”在柏林街头射击。
“心里怀着对战争的恐惧”
当弗利尤洛夫大尉在前线浴血奋战时,伊万尼辛和同学们不得不撤离到乌拉尔地区,在零下40°的严寒中完成学业。“我们穿着很薄的大衣,根本不暖和。从宿舍到教室要在刺骨的寒风中走2.5千米。教官说,‘你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训练,这在前线很有好处。’”伊万尼辛回忆,“他说的没错,在战争的头3年里,我只在像样的床上睡过两个晚上,而且是在医院,因为我的大腿被弹片击伤了。”但两天后,他拖着刚包扎完还未痊愈的伤腿毅然返回了前线。
“喀秋莎”很容易使用,一般训练一个发射小组只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就够了。几乎在弗利尤洛夫大尉牺牲的同时,伊万尼辛毕业了。接下来的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是与致命的“喀秋莎”一起度过的。
他第一次指挥“喀秋莎”作战是在1941年10月的莫斯科战役期间。当时敌人距离首都只有11千米远。“喀秋莎”连挖好观察哨位隐蔽起来,然后向着敌人打了两轮齐射。“我就站在那里,根本没有经验,手足无措。突然一发子弹就从这里飞了过去,”伊万尼辛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我们很快意识到,当德国飞机出现时必须隐蔽起来。”
最可怕的是库尔斯克战役,对“喀秋莎”恨之入骨的德国人每天都会追着伊万尼辛轰炸5~6次。“仅一次袭击他们就会出动50~80架容克-87轰炸机。那些飞机反复地在上空盘旋,直到炸弹声彻底沉寂下来。而我们只能躲在战壕里,或者钻到火箭炮车底下,”伊万尼辛此时的表情很无奈。但随后他又骄傲地说:“我们摧毁了许多坦克,应该有几十辆吧。”他比划着解释,火箭炮一次齐射就要打出几十枚炮弹,每个的重量都在60千克左右。“当击中坦克时,炮弹会当场爆炸。炽热的炮弹碎片会把它触及到的一切都燃烧掉。”
作为“喀秋莎”的指挥官,伊万尼辛经常会距离他的目标只有500~800米,肉眼就能看到被火箭弹炸得血肉横飞的敌人。“在火箭弹巨大的威力面前,我心中怀着对战争的恐惧。”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