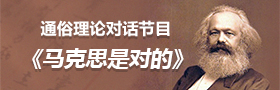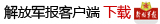1997年8月,我们《西南军事文学》举办了一次西藏“喜马拉雅”笔会。我们被汽车载上了海拔5380米的查果拉,见到了坚守在那里的生命群体─查果拉哨所的全体官兵。他们是这一生命禁区的征服者,他们也是这一生命禁区仅有的顽强生命。请关注今日《解放军报》的报道——

查果拉的鲜花
■裘山山
1997年8月,我们《西南军事文学》举办了一次西藏“喜马拉雅”笔会。途中,七八位作家驱车前往西藏海拔最高的哨所——查果拉。当我坐在颠簸不已时速却依然在每小时七八十公里的吉普车上向查果拉奔去时,微微有些激动。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査果拉。
同车的西藏军区作家许明扬告诉我们,查果拉原来的意思是土匪出没的地方,现在的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这两个说法我都听说过。但此时,在去查果拉的路上,面对满目荒山,面对在盛夏八月依然荒凉无比的群山,我对这两个说法都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因为无论是鲜花还是土匪,都是有生命的。而查果拉,是生命禁区。
我们被汽车载上了海拔5380米的查果拉,见到了坚守在那里的生命群体─查果拉哨所的全体官兵。他们是这一生命禁区的征服者,他们也是这一生命禁区仅有的顽强生命。
因为我们是从营部上山的,便为战士们带去了他们这段时间的书信和报纸。其中排长李春的信最多,有三封。于是大家要李排长交待,都是谁写来的?李排长从实招来:一封是父母大人的,一封是战友的,还有一封,他的脸红了:是未婚妻的。
战士们立即起哄,要求李春公布情书。出乎我的意料,李春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有幸在海拔5千公尺的高山上,在荒凉的不生寸草的地方,读到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情书的“作者”是位女大学生,她与李春通过发表文章成了笔友,进而成了恋人。就在我们去的时候,她已经从家里出发,分别乘火车、飞机、汽车向查果拉抵进,要在海拔最高处,举办一场婚礼。我想说,这是我所听到的最美的爱情故事。

李排长的情书,让战士们兴奋不已。图中读信者为本文作者。
查果拉到底是查果拉,没过多久,我们一个个就开始大喘气了,每走一步路都呼哧呼哧的,有两位还不得不抱上了氧气袋。但我们依然开心地和战士们一起开起了联欢会。
联欢会开始,李春排长就笑眯眯地对战士们说,我们先给作家们唱个歌吧,《鲜花献给查果拉》。
这歌儿我知道,是我们军区老诗人杨星火写的。每个查果拉的战士都会唱,每一代都会唱。当然,杨星火写的歌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妈的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那些传奇经历。我就和大家一起呱唧呱唧地鼓掌欢迎。
李春起了个头,战士们就唱起来——
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
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
歌声一起,我的眼泪突然涌出,速度之快让我毫无防备,身上连张纸巾都没有,只好用两只手去抹,结果越抹越多,满脸被泪水浸泡,不得不狼狈地离开会议室,离开正在大声唱着歌儿的战士们——
查果拉山高风雪大
山上自古无人家
……
歌声在荒无人烟的山顶继续飘荡。我跑出门外,躲在墙角继续流泪,我都不知道我的眼里竟藏着那么多的泪水。马上就有战士抱着氧气袋跟了出来,他们以为我是高原反应,让我吸氧。我抱歉地解释说,不是高原反应,一会儿就好了。
为了不让战士们担心,我努力克制着,重新回到了会议室。但面对那些战士的笑脸,面对他们干裂的嘴唇,我的眼泪还是不听话地往外涌。我低着头,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我无法对他们说清这泪水的出处,我只能把它归结为音乐的魅力。
接下来,作家刘醒龙喘着气为战士们唱了《小白杨》,作家王曼玲一边吸氧一边为战士们宣读了李排长的“情书”,让战士们开心得嗷嗷叫。只是因为缺氧,她念了几段就坚持不下,我又接续读信。我们的主编熊家海(已去世),则一个个地为战士们拍照。他们都给战士们带去了欢笑和快乐,只有我没出息,留下的是眼泪。
官兵告诉我,由于查果拉哨所海拔太高,来他们这里的女作家屈指可数。但是有一位女作家却来过很多次,可能有六七次吧,而且她还是唯一一位在查果拉住过的女作家。她就是杨星火。上个世纪60年代,查果拉哨所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杨星火很激动,写下了《鲜花献给査果拉》。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查果拉哨所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这首歌却一直留了下来,成为永恒的歌。每一批新兵来到哨所,首先要学会唱的就是这首歌。
后来我们登上了查果拉主峰。
在那片满是石头、看不到一点绿色的山坡上,作家邓一光忽然发现在石头的缝隙之间,生长着紫色的小花。他指给我们看,我们蹲下去,果然看到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像依偎着兄长那样依偎着石头,在冷硬的风中瑟瑟开放。
我惊奇地问它叫什么名字?有个战士回答说,它叫骆驼刺。我不相信。它看上去是那么娇小柔弱,和那高大粗壮的骆驼毫无相似之处,怎么会叫这个名字?那紫色的花瓣儿透明如薄薄的蝉翼,怎么扛得住这冷硬的高原的风?唯有它的果实很扎手,也许这就是“刺”的由来?
骆驼刺让我再次相信了奇迹的存在。不然你无法解释这不可思议的花。你无法想象它的种子是从哪儿来的,它是靠什么长出来的,它的细细的花茎为什么没被大风折断?它依傍的土地如此干硬,没有河也没有雨水,为什么没被渴死?
写到“渴”这个字眼儿,我忽然顿悟:它们是该叫骆驼刺,它们与骆驼不是形似而是神似,因为它们也和骆驼一样抗干耐旱,它们不仅从石头缝里长了出来,还努力地开出了花。
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杨老师,您写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每个上查果拉的兵都会唱。她很高兴,然后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地把歌词念给我听。
山歌唱给解放军
鲜花献给查果拉
……
我不会唱,我只能在心中一遍遍默想:骆驼刺也是鲜花,战士们的笑脸也是鲜花,杨星火老师也是鲜花。
两年后,杨星火老师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话。这位雪山诗人,不但是高原的女儿,还是一个藏族儿子的母亲。她的一生都与西藏息息相关,她的生命就是一首歌,永远在高原上传唱着。
査果拉的鲜花,是最美的花。
(作者小记:裘山山,女,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