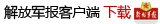“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记者访遵义会议会址手记
■赵传金 本报记者 张 良 特约记者 田胜平

遵义会议会址。 (据历史资料)
1921——1935,距离14年;
1935——1949,距离14年。
从时间维度上看,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到创立新中国时间轴线上的中点;从思想维度上看,1935年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拐点——“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如果说每个年份有一座“年份城市”的话,那么对于当时成立14年的中国共产党而言,1935年属于遵义。这一年,遵义因为一场会议改变了历史,因为一场会议永远地写进了历史。
6月5日,记者赶赴遵义,走进那场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址。
历史有其偶然性,但遵义会议的召开却是历史的必然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命运。古城遵义也是如此。
当年,自红军踏上长征路的第一步起,敌情就瞬息万变,在哪里战斗,在哪里落脚,在哪里开会,一切都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北依娄山、南临乌江的遵义并不注定与这场会议结缘。
所以,走进位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后,我们没有急于攀上当年开会的那幢二层小楼,而是走进了遵义会议陈列馆,试着去感知那场会议召开前的历史风雨。
“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指着墙上一张简单而醒目的图表,解说员王玉笛提及伍修权的一段回忆文字,把我们拉进了遵义会议召开前那段牺牲惨烈的历史。
图表名为“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损失表”,直观显示着那个时期的一组数据:红军从之前的30万锐减到3万,党员从30万减少为4万,根据地人口从1000万变成了100万……用毛泽东批判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三句话来说,就是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
回望历史,真理的地位从来不是天生的,而往往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对比才能最终确立。据刘伯承回忆,随着长征开始后我军接连失利,“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如果说部队上下这种强烈的情绪构成了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民意基础,那么遵义会议之前的三次会议则为此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
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猴场(今翁安县草塘),中央又一次否定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主张……
沿着历史的大脉络,从短短半个月间接连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这3次会议中“穿”过,我们感到,一场拨乱反正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已经势不可挡地从历史的必然逻辑中走来。
遵义,在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双重作用下,偶然又必然地与这场会议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