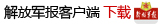斗争节奏在加快。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有二:一是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了行军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反对李德、博古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样就必须过乌江,彻底堵死了李德、博古的回头路。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是限制了李德在军事上的独断专行权。《决定》强调:“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而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重要的准备。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比前一年十二月间中央军委所作的《决议》,不仅更具法律权威性,而且其内容涉及军事指挥权的问题。
从此前两条路线较量的情况看,在拟议中的政治局会议上正确路线取得胜利似乎问题不大。但为做到万无一失,毛泽东提出把政治局会议变成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提出这一建议呢?“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就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这一建议被采纳。后来,参加会议的除了6个政治局委员和4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他们都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对李德、博古提出批评,保证了会议成功。
排兵。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也为落实早已决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供了时空条件。1月9日,中央纵队入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同一座楼上,随时交谈关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会上的斗争策略和三人发言的“排兵布阵”。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安排:在博古作了主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后,首先由张闻天发言开头炮。他的发言“提纲”是会前一个月来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形成的,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伍修权说张的发言提纲是毛起草的)。他分工负责系统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左”倾军事错误。为什么毛泽东执意让张闻天先发言呢?“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超过了博古,这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起来也更有说服力。”张发言之后,毛泽东紧接着发言,负责剖析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对“左”倾军事路线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继而王稼祥发言,主要是作补充,支持张、毛的观点,并提出更换军事领导,由毛泽东指挥红军的建议。他们预计连发三炮后,会带动一批人发言,并赞同对李德、博古的批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排兵布阵收到非常好的效果。王稼祥发言之后,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发、彭德怀相继发言,都支持张、毛、王的意见,“左”倾军事领导顷刻间全线崩溃。
策略。关于会上的斗争策略问题,在遵义会议“前奏”阶段毛、张、王也作了反复研究,形成了两点共识:第一,只讲此前军事路线的错误,不能讲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尽管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军事问题是头等重要而迫切的,政治路线问题可留待以后再解决;另外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而且与张闻天、王稼祥紧密关联。说政治路线错误,不仅牵涉面太大,而且张、王当时也不易接受。所以,毛泽东主张在会议上不仅不说政治路线错误,相反还要说“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第二,对待李德、博古要区别:对李德毫不留情,对他的“老子说了算”造成的严重军事错误,要严加批判;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对事不对人,对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领导人,尽量予以爱护,帮助他认识错误,以分化他们二人,孤立李德。以上这两条策略,毛、张、王在后来会议的发言中都加以贯彻,收到很好的效果。会后,博古认真思考大家的批评,不闹对立,不搞阴谋,逐步做到真诚拥护新的中央路线,为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李德这个“绊脚石”、“太上皇”则彻底被搬掉。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总之,遵义会议有一个内容丰富、构思周密的“前奏”,包括交谈、较量、排兵和策略等方面。万事俱备,只等开会。1935年1月14日,外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接电后急速赶到遵义。15日至17日,会议如期举行,这首宏大的交响曲便由“前奏”进入“高潮”。对“高潮”部分,已有许多论著详论,本文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