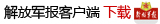597.9高地,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就是一串数字;对于懂得军事地形学的人来说,它是一个位置参数;但对于黄继光连的官兵来说,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激励,一种溶入他们血液的记忆,一种在98抗洪、汶川地震、国庆阅兵时遇到困难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钢筋铁骨,曾经想倒下又挣扎着站起来的那股不屈的精神,这就是黄继光连的597.9高地,这就是黄继光连的魂。
[连队档案]:1941年4月,在太行山区诞生,在华北战场与日寇展开长达4年的浴血奋战。1947年8月,连队随部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战役、西南剿匪等重大战役。1951年连队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六班长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1961年,连队随部改建为空降兵。和平建设时期,连队先后参加了’98长江抗洪抢险、08年汶川抗震救灾;“和平使命”等重大演习任务。连队19次荣立集体三等功、11次荣立集体二等功、4次荣立集体一等功。1991年5月、1998年9月、2009年8月,空军分别授予该连“空降兵模范六连”、“抗洪抢险先锋连”、“黄继光英雄连”荣誉称号。2013年8月,中央军委授予该连“模范空降兵连”荣誉称号。
你是不是六连的兵《士兵突击》里的钢七连连长高城经常问:“你是不是钢七连的兵?”黄继光连的官兵在遇到困难时经常问自己:“你还是不是六连的兵?”通常,他们问题的答案都一样:我是,所以我要撑下去。新兵郑瑞宇老家在河北邢台,黄继光参加抗美援朝时,就在那里举行的入朝誓师大会。郑瑞宇从小就是看着黄继光事迹长大的,来到军营的他没想到真的来到了黄继光连,还被分到了黄继光班。空降兵,是一支走在空中、打在地面,能超越一切地面障碍的特殊兵种。特殊的使命、特殊的任务、特殊的要求,需要经过特殊的历练。郑瑞宇没有想到,刚到连队,高强度的训练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这天中午,烈日炎炎。连长彭江林一声令下:“按要求披挂,进行全副武装奔袭!”战士们围着2公里长的训练场跑道,一圈、两圈…… 郑瑞宇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但他能感觉到,每向前一步,肩膀就被背囊勒一下,湿透的衣服不断摩擦着手臂和大腿腰部。每一次机械的迈步,都发出“呼哧”的声音,都在迅速地消耗着体内残存的一丁点体力,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班长,我实在坚持不住了!”身背30多公斤重装备的郑瑞宇再也忍耐不住了,死死地拉住彭江林的裤腿,用沙哑的声音恳求。“爬也要爬到终点!”彭江林一声断喝。这确实是一次令人恐惧的挑战——5圈、10公里远距离武装奔袭。之前,这是郑瑞宇无法挑战的训练禁区,他生得瘦弱却身负重荷。他别无选择,只能往前跑。他不停为自己打气,用尽一切办法节省体力,前进,前进。最后,他终于艰难地跑完了全程。连长彭江林在总结时说:“我们是空降兵,空降兵是干什么的?用《兄弟连》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天生被敌人包围的’。超常的战场需要我们有超常的能力,如果没有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战斗精神,没有迅猛快捷的战术动作,我们能打仗、打胜仗吗?更何况我们是黄继光班!你们看看你们自己,都成什么样子了?”大家相互瞅瞅,才觉得真有些滑稽:队伍里,没有了往日的严整;携行的装备,不是松松垮垮就是丢东落西。从那以后,郑瑞宇训练更加刻苦。战术动作不行,一趟一趟地体验;体能不是最好,休息时间“翻山越岭”;射击训练,一个姿势一练就是半天,枪口上吊着砖头,回到宿舍还要在门口挂一颗黄豆继续练;战术训练,仰望数十米高的刀削般的崖壁,一次一次往上攀爬,双手磨破了皮,鲜血渗在坚硬的岩石上,也不停歇。姜生武,四级军士长,连队最老的兵,入伍14年,至今仍在连队当班长,每逢连队有跳伞任务仍然带头从万米高空跳下。这位31岁的老兵从当兵就在黄继光连,历经了4任连主官,在2013年底还是选择留在了这个让他眷恋的军营,不为别的,就为自己是黄继光连的兵。采访中,他一口一个“老班长”叫着,起初我以为他说的是自己的班长,听了一会儿才听出来,他口中的“老班长”就是黄继光,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就像黄继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就像和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参加训练一起执行任务的老班长一样。每年新兵入营,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参观连队荣誉室,听的第一堂课是黄继光的故事,学的第一首歌是“特级英雄黄继光之歌”,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上甘岭》,执行重大任务都要在黄继光铜像前宣誓,在象征着黄继光献身精神的旗帜上签名;每晚连队晚点名,第一个是“黄继光”,全连官兵齐声答“到”。在“黄继光班”,至今还保留着老班长黄继光的床铺。
飞机跳伞的通行证 “这也叫黄继光连的兵?”在采访中,所有在黄继光连当兵的人最不想听到、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这句话。为了不听到这句话,再苦再累再难以忍受他们都硬着头皮上。空降兵有句口号叫“三肿三消,才上云霄”。意思是说,在跳伞训练中,双腿只有经受了从肿到消、从消到肿、再从肿到消的历练后,才有可能领取上飞机跳伞的通行证。仅地面训练,就够人喝一壶的了。教员一声令下:“离机——准备”,伞兵们就迅速将两腿分开,间隔20公分,身体倾斜65度,全身紧缩一团,双手抱在胸前。教员喊“跳!”,伞兵们便从1.5米高的平台上跳下来。有时,教员们为了让伞兵练就良好的“离机——跳”的姿势,只喊“离机——准备”的口令,一般人三分钟左右便大汗淋漓;十分钟左右,身体虚弱的甚至会晕倒。那一声“跳”,虽然没有在飞机上实跳的那种恐惧感,但也令人发怵,每天爬上跳下不下100次。按历年的训练经验,伞降训练用不了三天,准有人趴下。果不其然,训练第一天,就有一名新兵在“离机——准备”中昏倒了;在随后的“跳,跳,跳”中,新兵们的腿都肿了。吃饭时,扶着桌子才能坐下去,吃完饭,靠人拉一把才能站起来,走路时腿不听指挥,下坡得侧着身子小心翼翼。黄华午,大学本科毕业,怀揣着“预定线路”来到部队:当兵两年,混个经历,入个党,回家好安排工作。伞训中,要求两腿并紧,着陆时膝盖、脚尖和脚跟三点不开。可他的腿就是不争气,还没有接触地面就哆嗦开了,动作总是不标准。连长彭江林反复讲解,他总也掌握不了。彭江林急了,他就哭了。训练中有一个课目叫飞跃自我。一根高6米的杆的顶端,连接着一个直径20厘米的圆盘,官兵们要一步步爬上高杆的顶端,站在圆盘上,在大风的左摇右摆中用力跃进,抓住1.5米外的一根长约1米的横杆。6米的高度、左摇右摆的圆盘、宛如风筝的身体、毫无依托的横杆,无一不在考验着参训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与胆识。生得瘦弱而胆小的黄华午好不容易壮着胆子爬到了圆盘,却再也没有勇气完成那充满惊险的一跃,只好又顺着杆子爬了下来。就是这样一个兵,在黄继光连被练成了标兵。连队的一次新伞型跳伞演练。随着地面指挥员一声令下,只见一个个小黑点冲出机舱,窜入云霄,直线下落。1000米、800米、500米。“不好,伞没开!”地面指挥中心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打开备份伞,打开备份伞!”整个着陆场都紧张起来,大广播、小喇叭,一致对天,指挥员们喊破了嗓子,大家本能地朝着一个方向,一起拼命地跑去。“不好,伞没开。”黄华午离机后吃力地抬起头,看到战友们的伞都张开,而自己却成一条直线下降。 “ 飞伞!”飞伞是伞具上的一种特有装置,当跳伞员发现主伞张开不正常时,可拉开飞伞装置,飞掉主伞打开备份伞自救,这就要求跳伞员有着高超的跳伞技术和超人的胆量。只见黄华午迅速伸出右手臂,顶着风,瞬间拉出飞伞手柄,使得人伞迅速分离,在身体产生失速、后仰的同时,快速拉开了备份手拉环,没等黄华午反应过来,“嘣”的一声,伞开了。黄华午凭借着自己的勇敢,果断处置,3秒钟内,连续做了5个动作,终于安全着陆了。从一个别人口中的“孬兵”成长为大家眼中的标兵,黄华午自己说:“就是不想让别人在背后说黄继光连的兵其实也不怎么样!”
真正的空降兵是摔打出来的真正的空降兵,就是在常人难以领略的艰难、恐惧的生命状态中摔打、磨砺出来的。每年,两伞相插、主伞不开、伞绳缠绕等险情时有发生,但黄继光连的兵从没有埋怨过,也从没有让人失望过。那年,黄继光连担负起超低空跳伞试训任务。超低空跳伞,素有闯“鬼门关”之称。因为,从空中自由落体到地面仅有几秒钟,只要稍有差池,危险就会伴随而至。试跳展开不到两天,就连续发生两起险情,一下子使连队迅速展开的脚步变得迟疑了。训练暂停还是继续?继续,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就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停下,虽保险,却会延误新的作战能力的形成。《世界空降战史》记载:空降兵战斗减员,70%的伤亡都是在空中滞留时间过长造成的,而超低空跳伞能有效缩短滞空时间。经过从伞具到技术等方面的再次论证后,他们决定:训练只能加紧,不能停止。“跳、跳、跳”经过数十次的跳伞摔打,他们成功地征服了空中“死亡地带”。 “只要任务交给了黄继光连就没有完成不了的。”黄继光连所在团政委田新在接受采访时说。 2013年七月初,一场新型伞试跳训练拉开帷幕。上午九点,战鹰掠过,黄继光连官兵从天而降,天空顿时绽放开一朵朵洁白的伞花。只见官兵们在空中时而呈“S”型飞行,时而螺旋下降,在离地还有一定高度时,迅即端起手中武器对“敌”猛烈射击…… “新伞型释放了以往身前备份伞的空间,便于我们携带武器,空中就能对敌射击。”着陆场上,黄继光连伞训长刘杰对全连空降训练情况进行小结。记者了解到,所谓的“换手”训练,是指让连队每名战士分批轮换进行配备空降兵的所有机型、主战伞型的跳伞强化训练。 “换手”训练源自一次教训。在2013年上半年上级组织的一次突击性空降演练中,他们连部分官兵居然因为没有跳过某型运输机而被排除在任务之外。事后分析,原因是平时新机型、新伞型试跳等风险性高的任务都让素质好的战士顶上了,导致普通战士空降技能“瘸腿”现象严重……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连队顶着巨大的风险,计划让全连官兵所有机型、所有伞型挨个轮训一遍。这次跳伞试训,他们还按实战标准从难从严设置跳伞条件,成建制完成260米超低空跳伞,使用4种机型3种伞型开展跳伞训练,伞降作战能力取得新突破。
第N次拿下空降兵部队的第一黄继光连,作为中国唯一一支空降部队中的尖刀连,代表着中国空降兵的形象和实力。在空降兵历次战斗力转型的紧要关头,六连始终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 1962年,该连随部从步兵改建为空降兵,全连官兵仅用67天成建制完成首次跳伞,率先实现了从传统步兵连到空降摩步连的转型; 1990年,他们率先完成某大型运输机和某新型伞三门四路试跳任务,加速了部队战斗力转型的进程;如今,该连官兵具备在多种机型、多种地形上运用多种方式跳伞的能力。他们在原始森林、高原、海岛、水网稻田跳伞,都是一次成功,为大部队在各种地形跳伞闯出了新路,填补了中国伞兵史上一项项空白。近10年,该连摸索总结的十多套训法战法被空降兵部队推广。2013年年初,空降兵在某大型运输机和新型降落伞上进行战斗力整合空降实战试训,黄继光连挺身而出,担当起试训任务。黄继光连官兵深知摆在自己面前的风险:新型飞机、新型降落伞,一无数据,二无经验,三无教材;披挂系统最重达几十公斤,人的身体能否承受起这种冲击力,这一切都靠大家用生命去探索。 “站着是根桩,躺下就是梁,六连何时当过孬种。”探索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自受领试训任务以来,六连官兵每天比太阳起得早,比月亮睡得晚,中午晚上连轴转,他们向飞行员学习,了解新飞机的飞行参数与结构特点,向生产厂家咨询了解新型降落伞的技术指标。伞训骨干何晓斌为了精确计算各种空降数据,不分昼夜泡在图书室查阅各种资料,吃饭睡觉都在琢磨,短短一个月内体重掉了三公斤。在此基础上,他们按照战斗编组以及携、运、行中的运输条件和要求,对连属武器弹药一件一件组织、一箱一箱编组捆绑。他们还根据组合中的实际情况,大胆对个别战斗编组进行变更。终于,伴随着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次次的地面准备,一项新纪录又在六连产生了——空降摩步连首次成建制新型机、新型伞、新装备披挂武装跳伞成功,为步兵连队全员全装空降作战闯出了一条新路。盘点六连参加的数次重大演习:海岛登陆、山地进攻、城市作战、空中进攻、伞降与机降结合、昼间空降与夜间空降交替、不同机场不同航线多种机型多个波次的协同空降,六连富有创新意义的好戏在蓝天大舞台上连篇上演。翻开连队的荣誉薄,历数赢得的57面锦旗,六连,凭借现代军人之勇,把“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冲天豪情写上了万里云天,打造出更尖锐、更锋利的“刀锋”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