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贺麟 资料图片
垂范立教 桃李春风
——作为教育家的贺麟
■郭继民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1919年入清华学校学习。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攻读西方哲学,获奥柏林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黑格尔理则学简述》《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译有《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伦理学》等。
贺麟先生1992年去世后,中国社科院出版纪念文集,对贺先生的评价为:“贺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国内外久享盛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翻译家。”(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3年)此评价固然妥当,然似忽视了贺先生“教育家”的身份。贺先生老家成都金堂的“贺麟纪念馆”,在对他的介绍中增添了“教育家”的称号,但鲜有人以此视角深入探究。
贺先生之所以称得上“教育家”,并非因其名扬天下且具有教师身份,而是基于其在哲学教育上的卓越贡献,务实的教育理念,以及知、情、意相融的教育实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贺麟(前排中)与学生在一起。 资料图片
培育一流人才
贺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一流人才,支撑起一段时间内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半壁江山,可谓贡献卓越。1992年,学界举办会议庆祝贺先生九十岁寿辰,百余位学者出席,皆是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弟子洪汉鼎曾对到场的贺门弟子进行分期:第一代学生有任继愈、熊伟,可能还有苗力田、齐良骥、王玖兴;第二代弟子有王太庆、陈修斋、汪子嵩、杨宪邦、张世英、张岂之、杨祖陶及劳思光等;第三代弟子有叶秀山、梁存秀、王荫庭等;第四代弟子有王树人、洪汉鼎、薛华等;最后一代弟子有宋祖良、范进(范建荣)等。其实,在第四代、第五代之间,尚有张祥龙的加入,祥龙先生虽非“形式上”的学生,却是“亲炙弟子”。若再加上贺先生指导的翻译人员,这个名单还可延长。梁存秀则认为贺先生的弟子有八代之多,上述名字还应增添周辅成、乔冠华等人。
诚如洪汉鼎所言,“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的研究大部分就是靠这五代的学生”(洪汉鼎《贺麟教授与我的哲学生命》)。当下,中国大陆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许多优秀学者都是贺先生的再传弟子,如杨祖陶的弟子邓晓芒,齐良骥的弟子韩水法,苗力田的弟子李秋零,叶秀山的弟子黄裕生、吴国盛,熊伟的弟子陈嘉映、王庆节。经过“代际”转换,新一代学者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涉及德国古典哲学、解释学、现象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
昔日孔子三千弟子,贤者七十二,被尊为大教育家;今朝贺先生成名弟子当不下七十二,有此贡献,称其为优秀教育家当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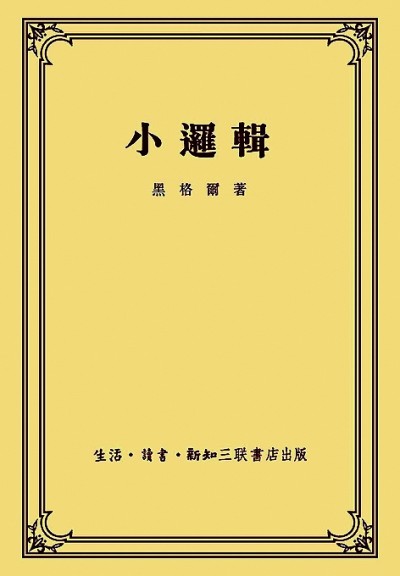
▲贺麟译作《小逻辑》。 资料图片
务实的教育理念
贺先生能取得如此的教育成就,与其深厚学识有关,亦与其务实的教育理念相关。贺氏虽未专门从事教育研究,亦未写过大部头教育学著作,但他提出了一系列深具可行性的教育理念。
传统观念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贺麟先生则有“十年树人”之理想,这源于他1946年返乡之感悟。离乡十年,房前屋后树木如故,而乡人则面目全非,于是贺先生提出“十年树人”的理想。他认为,一个好的学校,一个大教育家或政治家十年尽力教育,即可达到深远伟大之效果:曾国藩十年内就培植了许多人才,在政治军事诸领域产生很大影响;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后不过六年,即培育出许多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人才。
如何实现“十年树人”之理想?贺先生提出一系列教育观念。他认为,首先要变传统的“学问全在书本”为“学问既在书本亦在实际的劳作和服务之中”,要重视书本以外的肢体活动,将劳力与劳心结合起来。其次,改变传统“士或学者为独特阶层”之观念,以后“一切职业都将学术化”。以前人们言“耕读传家”,今后亦可言“工读传家”“商读传家”甚至言“兵读传家”,因为任何活动皆需学术指引。再次,要摈弃“读书为做官”之陈念,树立“读书在于求得真实学问”之新旨,此为教育理念的根本改变。贺先生指出,新式教育当谓“价值教育”,既包括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纯粹文化价值,亦包括服务社会大众的“实用”价值,人们读书须围绕以上价值用功。此外,贺先生还对不同阶段的教育重点提出洞见。比如,就教育重心言,小学阶段应注重生活,中学应严格训练,大学应重视真正的学术;以德育言,小学应重乐教的陶冶,中学应重礼教的约束,大学则重诗教与信仰的熏沐。上述见解,对今天的教育亦有重要启迪意义。
在“教”“学”这个对子中,贺氏认为:学为主,教为从。首先,“有学自然能教。学有心得,自然不期教而能有教的效果。学不进步,虽名为教师,而终无以符教师之实”。其次,“教育是为人,学是为己。教人是做教师的天职,求学是做人的天职”。
既然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学”,而“学”很大程度上主要靠阅读,因此掌握好的读书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贺先生对此颇为重视,曾撰写《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在该文中,他强调“读书、做学问贵自用思想”,“自用思想”当知晓“思想的方法”。思想的方法,即逻辑的方法、体验的方法及玄学的方法。其中,逻辑的方法能使思维严密系统,避免散漫支离;体验的方法,可使学问具备亲切、丰富之内容,避免枯燥;玄学的方法,能促使人们养成远大圆通之哲学见识,以消除偏执。在分析思想方法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读书三法”,即逻辑的方法、体验的方法及“互观法”。逻辑的方法旨在把握全书之推理线条;体验的方法则以作者视角“涵泳其中”从而得其真义;“互观法”即“由全体观部分,复从部分观全体”,通过“由约而博、由博而约”之路径博涉作者其他相关著作(甚至包括同时代与此相关的著作),以便在整体上给著作以客观定位。“思想法”与“读书法”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既点出思想路径,又兼“知行合一”精义,整体上彰显了黑格尔辩证法精髓。
除了上述通用的读书方法外,贺先生还将治学经验传授给学生:一是要科班出身,二是要从“一点”做起。科班出身,强调学哲学须经严格的思维训练,否则容易流于散乱,不成体系;从“一点”做起,则言做学问之初切勿求广,要学会聚焦,从“一点”做起。活跃在哲学界的中坚力量皆为“科班出身”(接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借此理念,哲学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者。又,当今学界,成绩斐然者大抵从“一点”做起,如:康德之于邓晓芒,海德格尔之于孙周兴,胡塞尔之于倪梁康,皆是从“一点”做起而成就卓然之范例。

▲贺麟著作《黑格尔哲学讲演集》。 资料图片
具体到西方哲学的学习,贺先生给出“直捣黄龙”“学译结合”的慧解。贺先生主张,读书学习贵在掌握第一手资料,故须“直捣黄龙”。外国哲学之“黄龙”乃作者以母语写就,故贺氏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至少会一门外语。若不懂外语,只读他人翻译的作品,就可能跟着译者走;若译者错译、误译,读者则离“真义”远矣。
克服语言障碍后,要尽可能去翻译原著。贺先生认为翻译工作并非仅是简单的语言学问题,它还意味着译者不仅要像作者那样思考问题、真切地进行哲学训练,而且还须调动自身的语言能力,按照“信达雅”的原则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因此之故,翻译哲学著作亦是在认识、理解基础之上的深层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创造性的工作,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在贺先生的“学译结合”理念的教诲下,他的学生王太庆、王玖兴、杨祖陶、陈修斋、王子嵩、苗力田、洪汉鼎、范进等,翻译了西方自古希腊以降的主要哲学著作,为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再传弟子邓晓芒、李秋零、韩水法等人亦承“祖训”。其中,邓晓芒先生与其导师第一次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从德文译出,李秋零教授近乎以一己之力翻译了《康德著作全集》,韩水法教授则独自从德文翻译了康德的“第二批判”,三者亦因此而成为康德研究的专家。
贺先生一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不强迫学生顺从自己。张世英大学毕业保送研究生,选择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贺先生见到他,并没有责怪,反而笑着说,“原以为你会选择北大研究院,跟我研究黑格尔;也好,各有千秋,跟金先生(金岳霖)学分析哲学,会做出很好成绩的。”(张世英《引领我走向哲学的贺麟先生》)其实,除了杨祖陶、王玖兴等少数弟子以黑格尔为研究对象外,贺麟的多数弟子选择了其他研究方向,比如,洪汉鼎转向诠释学,王子嵩选择了古希腊哲学,苗力田成为亚里士多德专家……
贺先生之所以持此开放立场,与其学术追求有关。贺先生认为读书做学问“贵在追求真理”,既然如此,无论研究德国哲学还是其他哲学,它们皆是追求真理的工具,或曰皆是哲学研究的平台或手段——贺先生认为做哲学当研究“哲学本身”,而非要成为“研究某某哲学”的专家,故而对弟子从不设限。事实上,他本人亦是开放的,早岁醉心于心学,中岁聚焦于“黑学”,晚年除了翻译黑格尔哲学著作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贺先生的开放立场也与其“思想贵在创新”的主张有关。他在《论哲学纷无定论》一文中明确指出,真理也许只有一个,然而鉴于追求真理者的认知能力、经历、立场、方法等因素,其不同阶段将得出不同的看法,故言“哲学纷无定论”;反过来讲,假设哲学有定论,正是哲学的末路,势必扼杀人们的创造力。言“哲学无定论”并非意味着学哲学的人可以信口开河,胡言乱语,更不是说“每个哲学家没有他自认为苦思力索深信自得的真理”,而旨在“注重哲学的批判怀疑,以求思想的自由创新”。贺先生鼓励学生自由地创新,曾撰写《向青年学习》,即是明证。据弟子回忆,贺先生的两句口头禅之一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句为“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若将老师之是非定于一尊,弟子又将如何超越老师呢?
贺先生的开放立场还与黑格尔的影响有关。贺先生固然倡导直面哲学本身,但深受黑氏影响亦在情理之中。黑氏谓真理乃一整全过程,个体之所得,充其量不过是真理之局部;局部之真理颇似“盲人摸象”,仅得一端,当然不能定于一尊。故追求真理者当具开放心态,不可画地为牢。
贺氏的教育理念虽寥寥数则,却直中要核,且极具哲学意蕴。

▲贺麟著作《文化与人生》。 资料图片
知、情、意相融
陶行知先生认为,真正的教育家须将“知、情、意统一起来”。贺先生当然熟稔“知、情、意统一”的哲学内涵,他在教育学层面虽未言及此,但一生躬身践行了这个理念。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做到了“授知融情”。贺先生学贯中西,乃学界翘楚,故能吸引青年才俊汇聚门下。任继愈曾回忆,贺先生在西南联大授课时,曾到其他学校兼课,当他回返西南联大时,好几名同学主动转学,跟随贺先生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张世英先后在西南联大经济系、社会系就读,直到选修了贺先生的哲学概论课,才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转入哲学系。
贺先生缘何有此魅力?“是贺先生讲课的技术特别高超吗?当然,就这方面说,贺先生也是一位好老师;但就讲课技术而言,即使当时政校教师中比贺先生好的也不乏其人。”(陈修斋《回忆贺麟先生》)陈修斋先生认为,贺先生具备“一种难以言传的、以自己对所讲内容的真诚而潜移默化地感动人的精神力量”。譬如谈及晦涩的黑格尔思想,贺先生即以浪漫抒情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即为其对“对立统一”和“扬弃”之辩证法思想的恰切解释,其中既有贺先生的独特理解,又含其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以“中”通“西”),颇能引起学生共鸣。
贺先生“上课采取闲谈的方式”(陈修斋语),他总是娓娓道来,这种平易近人的授课方式拉近了师生的情感距离,能抓住学生的心,使学生处于自由的状态。诸弟子回忆恩师授课之场景,皆以“如坐春风”描述之,其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此亦为贺氏“授知融情”之日常体现。
贺先生的“授知融情”还表现在其崇高的师德上。梁存秀在《回忆吾师贺麟》一文中提到,《小逻辑》第二版出版后,北大研究生班的同学通过党支部书记请贺先生为他们讲解此书,并准备付给他若干讲课费。贺先生欣然同意授课,讲了六次,但是他拒绝接受课酬:“我是北大的教授,你们是北大的学生,传授学业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谢谢你们,但绝不能收这个报酬!”拒绝授课费的背后,实则融入了贺先生尊重知识、尊重学生的高尚师德,这当然是伟大的情感。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也做到了“以情涵意”。范进在贺先生120周年诞辰会议上,道出学生们的共识:贺先生“仁智”并举。先生之智,世人言之甚多,姑言其仁。仁者,爱也,发而为情,则表现为对弟子的宽容之情、佑护之情与“坦诚之情”。
西南联大时期,贺先生家中常有学生造访。据汪子嵩回忆,几位同学曾就“黑格尔哲学到底该联系朱熹还是王阳明”的问题与贺先生争辩起来,让老师有点不高兴。然而,下次同学到家中上课时,贺先生依然尽量帮助同学,贺师母还给同学做点心吃。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有中专文凭的张祥龙问学于贺先生,贺先生不但予以系统指导,更以平等、亲切的态度与其交谈,“他眼中没有我的幼稚、偏执和可笑,而只有那慢慢显露出来的精神生命”(张祥龙《我与贺麟的师生缘》)。贺先生对学生的包容、宽容之情可见一斑。
自西南联大返京后,贺先生曾担任北大训导长一职,在这个岗位上设法保护学生。无怪乎北大学生自发地送锦旗给贺先生,上书“我们的保姆”五个大字。贺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会”,最初几名成员中,汪子嵩、邓艾民、黄楠森三人都是地下党员,有人向贺氏告状,他置之不理,佑护之情尽在其中。
贺先生历来对学生坦诚相待。新中国成立前夕,贺麟先生被国民党列入首批“转运”名单,汪子嵩受命挽留先生,不惜“冒险”说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贺先生不仅对国民党当局守口如瓶,且最终接受学生的建议留在大陆。任继愈回忆了先生的另一种坦诚:贺先生谈到曾国藩与其师倭仁交换日记的美谈,故邀任继愈同其交换日记,以此相互促进。日记作为私密之物,贺先生却能于弟子面前敞开心扉,毫无遮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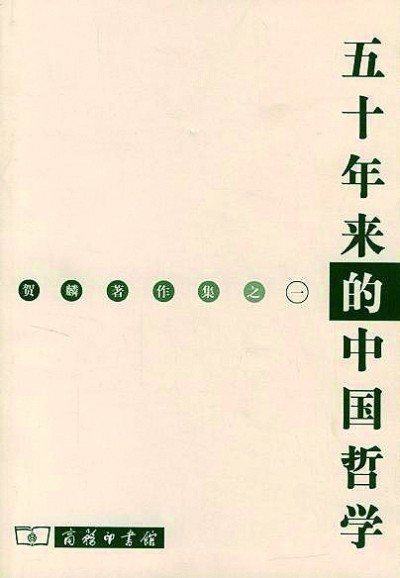
▲贺麟著作《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资料图片
情感背后,蕴含深意——贺先生并非毫无原则地滥用情感,他始终将情感与激发学生追求真理的意志结合起来。换言之,无论学生是何种身份、有何种立场,只要以追求真理为务,贺先生都是支持、鼓励的。洪汉鼎遭遇坎坷时,贺先生给予力所能及之帮助,并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信鼓励:“你今后能以古典哲学为重点,深入系统研究,很好。但须知德国古典哲学与生活实际关系密切……”关爱、鼓励学生追求真理之意,尽在情感之中。
在教育实践中,贺先生还做到了“以意进知”。意即意志,按康德的说法,即是自己实现自己对象的能力。因此,“以意进知”,首先表现在“主体在实现自己对象过程中的学习能力”。贺先生本人即“以意进知”的典范。他在研究德国哲学时就立下了翻译黑格尔哲学的“意志”,此意志被他视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尽性”之事。在耳提面命中,弟子亦被此“意志”(指“翻译著作”)所感染、调动。譬如,杨祖陶为完成此黑格尔的《耶拿逻辑》,八十岁高龄仍在“劳作”,在完成老师“意志”之时,也尽了“己之性”。
“以意进知”也表现为“意志”激发“干劲”。持“心学”立场的贺先生,认同美国哲学家詹姆斯“信念产生干劲”之信条,故而尽量鼓励学生。叶秀山北大毕业后,在贺麟先生“麾下”工作。叶秀山一度对美学产生兴趣,欲离开哲学所。贺先生“拦”住了他,并告知他毕业分配之原委:叶的毕业论文未得到指导教师郑昕先生的认可,成绩只同意给“中”,故未能留在北大。贺先生认为叶脱稿亦能把问题说清楚,故坚持给了“良”,并将其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贺先生还劝他,“研究美学要有哲学史基础,你先在这里学一年哲学史,一年以后再考虑转”(叶秀山《我是怎样喜欢起哲学来的》)。此种意志上的鼓励对叶秀山影响极大,诚如叶氏所言,“他当时这一拦,对我以后在学术道路上的进步关系太大了”。换言之,叶秀山的“干劲”是被贺先生激发出来的。
“以意进知”还表明“追求真理”之意志。20世纪30年代,贺先生作《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旨在以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启蒙并激励国人,此书读者对象不仅限于学生,而是针对四万万同胞,故其教育作用大矣。又,贺先生所秉持的“读书当追求真理”亦是一种意志,此意志俨然成为一种精神,传承于其弟子间,亦传承于未曾谋面的“私淑弟子”之中。
“立功”“立德”“立言”是古儒追求的“三不朽”。若从教育的视角观之,贺先生的“师功(人才培养)”“师德”“师言”之成就,皆达到了相当高度。
(作者:郭继民,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