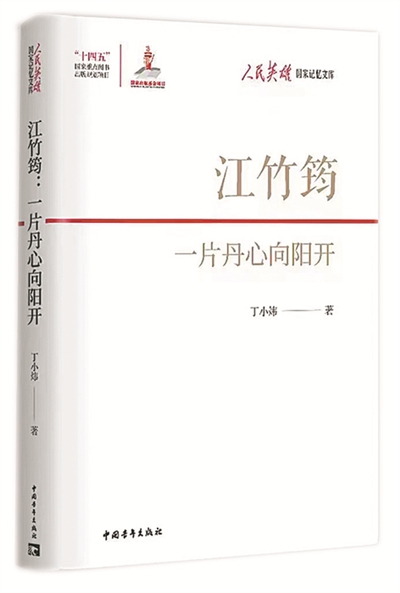
历史文学写作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依然保持新鲜和悬念,在推陈出新中无限接近和抵达历史的现场和真相。军旅作家丁小炜历时两年创作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新作《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们打开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探索创新之门,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精神的力量和生命的真理,那就是穿越时空获得永生的不是物质,而是永远的信仰与不朽的信念。
历史值得重温,英雄必须缅怀。丁小炜在决定采写《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之前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创作的难度和挑战。诚如他在本书的后记《她依然活在珍贵的人间》中所说:“江姐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关于她的纪实文学作品有很多。正因为这一点,采写这个人物有很大难度,难以‘鲜为人知’。而我毅然决然要写江竹筠,则是因为我的故乡——重庆云阳,那是一片深情的土地。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烈士是我们重庆云阳人,我从小就听到很多他们在云阳从事革命活动的故事,因此无论困难多大,那种写作的冲动依然在心底澎湃。”
带着这份清醒的觉悟和清晰的思考以及澎湃的激情,丁小炜从自贡到成都、再到重庆、云阳,沿着江竹筠出生、成长和革命的道路,小心翼翼地探访、毕恭毕敬地聆听、认认真真地做笔记,走遍了与江姐有关系的所有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和故居、故地,采访到了健在幸存者和亲历者,倾听到了许许多多含情含泪的讲述,获得了诸多过去文学图书和教科书中、艺术舞台上都没有表现和呈现的信息和形象。于是,一个洋溢着青春理想,一个怀揣坚定信念、大义凛然的江竹筠就从血雨腥风的历史深处走来,从他的笔下走了出来。
英雄人物的传记类报告文学写作,如何突破编年史和史料铺排式的写作套路,是文学创作面临的艺术和技术性难题。《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大胆摆脱了历史时空的限制,突破传统英雄叙事的格局,巧妙运用插叙、倒叙的手法,在“破”中求“立”,以“形散神不散”的散文样式,从“我”的第一现场视角,在追寻、回溯、沉思、仰望中实现了饱含深情又张弛有度的叙述,让英雄在简洁、干净和诗意的文字中“复活”,从而达到还原历史和启迪当代的写作意义和价值。
作品以《狱中,她写下托孤遗书》开篇,就起到了别具一格又开门见山的效果。我们知道,共和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对江姐的印象多来自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歌剧《江姐》,而历史文物尤其是前些年才公开披露的“遗书”则能为我们还原更加真实的江竹筠。面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和丈夫彭咏梧的牺牲,在渣滓洞中,在这封“托孤遗书”中,江姐写道:“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地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活着。”读着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这个身材娇小的四川大学女学生、这个深爱丈夫的妻子、这个给襁褓中幼子留下遗训的柔肠母亲、这个以热血坚守红色信仰的女中豪杰,怎能不戳中我们的心、湿润我们的眼睛?
要想完整地讲述江姐的革命人生,就必须要讲述她的丈夫彭咏梧烈士的革命生涯。这对本书的作者丁小炜来说,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故乡的革命烈士,少年时代就敬仰的英雄彭咏梧自然是他文学创作和精神的闪亮坐标。因此,在《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一书中,我们不仅阅读了《她从江家湾走来》,也读懂了《他从彭家湾走来》,从而更加完整、全面、立体地理解了这个《特殊家庭》。在作家这种巧妙地从“地理坐标”到“情感坐标”的结构安排中,更让我看到了江姐的“一张住院单”。丁小炜以“在场”叙事的方式作了历史的记录:
在四川大学江姐纪念馆,我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编号为36986的《住院病人记录》单子。
这是一张70多年前华西协合大学医院的住院单,其中,中文记录的内容为:彭江志炜,女,24岁,已婚,省籍四川,诞生地点重庆,现住址为望江楼川大女生院;科别为产科。英文记录的内容为:入院日期1946年4月18日,出院日期1946年5月10日;诊断为contracted pelvis(骨盆狭窄),手术为classical cesarean section & ligation of tube(古典式剖宫产和输卵管结扎)。记录者的习惯和娴熟的英文书写,透出浓重的教会医院文化背景。
这份住院单传达的信息让我们穿越岁月的尘埃,触碰到了一段令人心生感动和崇敬的历史。我们仿佛看见黑白光影中,江竹筠在医院生产的那些日子,甚至听得到医院外川味浓郁的叫卖声和成都老街区的嘈杂,1946年春天那明晃晃的阳光仿佛正洒到我们脸上……
江竹筠要生孩子了。黄芬、黄芳和同班同学董绛云找来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了华西协合大学医院妇产科。由于骨盆狭窄,江竹筠遇到了难产,医生诊断必须做剖宫产手术。没想到的是,临做手术时,江竹筠恳求医生:“大夫,请一并给我做了绝育手术吧!”医生十分不解:“你这是头胎,哪有生头胎就做绝育的?”一旁的几个姑娘也诧异万分。
江竹筠再三坚持,医生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
江竹筠生下一个胖胖的男孩。半个月后,彭咏梧从重庆匆匆赶来。如江竹筠所料,得知她做了绝育手术,彭咏梧表示理解。老家在云阳,孩子又生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决定给这个男孩起名“彭云”。
今天回想,江竹筠做出这样的决定,心里肯定也有挣扎。作为一个母亲,她一定想多要几个孩子,但面对斗争越来越残酷的现实,孩子多了就成了工作的拖累。再者,地下革命工作者随时都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她是有准备的。在那样的年代,人们思想还不开放,江竹筠能有那样的抉择,甘为革命作出舍弃,真让人无比敬佩。
丁小炜在书中向我们、也是向时代提出了一个反问:“一张住院单,我们读出了什么?”作家在采访写作中不断地寻觅、不停地沉思,他在后记中再次追问:“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身陷黑暗而内心充满光明,是什么让他们面对酷刑而眼里无比平静,是什么让他们品味到了信仰的芬芳,是什么给了他们一往无前的力量?”是啊!作为后来人,我们应该读出什么呢!革命理想高于天。毫无疑问,江姐的革命故事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永垂的信仰与不朽的信念!
英烈从何而来?渣滓洞里黑暗与光明的变奏、忠诚与背叛的对比,让我们更加懂得了什么叫信仰、什么是信念。一片丹心向阳开,不忘初心向未来。在丁小炜的这部作品中,29岁的江姐江竹筠和她的丈夫彭咏梧用他们短暂的人生和宝贵的生命,以“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和“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践行了“红岩精神”。
傲骨红梅,千秋不朽!当我即将完成这篇评论写作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这个日子(8月20日)正好是江姐102岁的生日,内心油然而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和神圣,情不自禁再次缓缓翻开书页,凝望着照片上永远年轻的可亲可爱可敬的江姐,忽然发现一种穿越百年的美丽袭击了我的心灵,如同灿烂的阳光穿过云层照亮了我精神的大地和天空。我知道,那是人民的大地和英雄的天空,晴朗、蔚蓝、深远又辽阔……
(本文刊于《解放军报》2022年9月3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