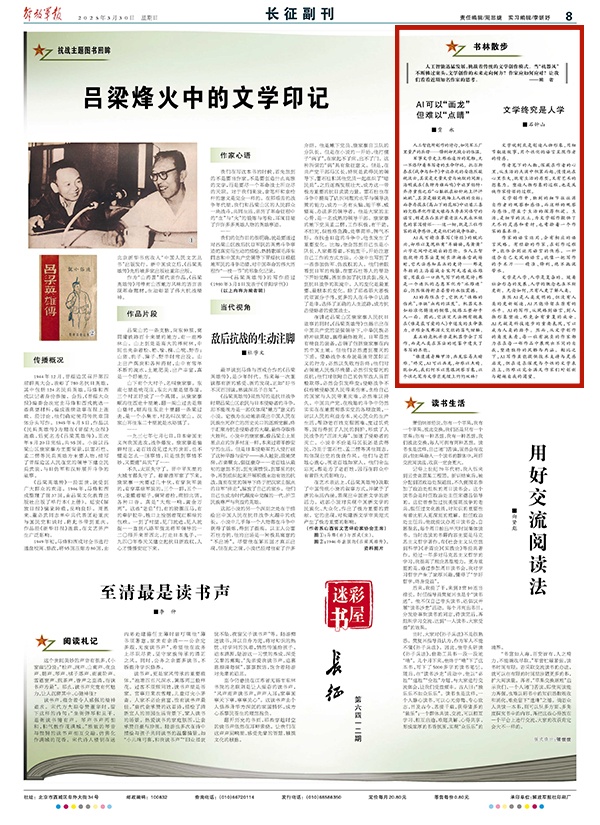书林散步
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挑战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当“机器风”不断拂过案头,文学创作的未来走向何方?作家应如何应对?让我们看看近期知名作家的思考。
——编者
AI可以“画龙” 但难以“点睛”
■贾永
人工智能所创作的诗句,如同军工厂里量产的兵刃——锋利却无战士的体温。
军事文学史上那些凌厉的笔触,无一不烙印着书写者的生命印记。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让垂死的安德烈凝视流云,其实是丈量天堂与地狱的间距;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让罗伯特·乔丹重伤之后“心脏抵在松针地上怦怦地跳”,其实是锚定战场上人性的坐标;而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环》中让梁三喜的欠账单化作梁大娘与玉秀共同恪守的诺言,则是在凸显沂蒙老区人民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这一切,既是三位作家的战争感悟,更是他们的战争体验。
AI或可精准摹写《诗经》的赋比兴,却难以复现杜甫“车辚辚,马萧萧”六字之间呼之欲出的悲怆。当人工智能软件用算法复制长津湖冰雪战场时,它无法感知真正的史诗——那是年轻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冻成冰雕前,用最后一口热气写下的绝笔诗;那是一个连队的志愿军化为“冰雕连”后,仍然保持射击姿势的永恒震撼。
AI的局限在于,它既无“性格的伤疤”,亦缺“血肉的温度”。机器文本如标准化铸造的铜像,纹路工整却千人一面。因此,它注定无法拥有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迸发的生命张力,亦难企及那泪火交织的荡气回肠。
真正的危机并非是机器学会了写作,而是人类在算法的迷雾中遗失了书写的本能。
“谁遣通身鳞甲活,画龙容易点睛难。”终究,AI可以画龙,却难以点睛。既如此,我们何不以慧眼洞察万象,以个性之笔为文学巨龙缀上灼灼双眸?
文学终究是人学
■石钟山
文学说到底是创造人物形象,用细节叙述故事,用个性化的语言呈现作者的情感。
作者笔下的人物,深藏在作者的心里,从生活的点滴中积累而起,慢慢地在心里长大,既有生活的原型,又有艺术的想象力。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也是反映作家情怀的过程。
文学创作中,独到的细节往往源自作者的观察和感悟,而这样的观察与感悟,得益于生活的深厚积淀。生活,是细节的沃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素材,也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基本功。
作家的语言运用,会有相应的语言风格。有经验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能体会到运用语言的快感。一种适合自己文风的语言,就像一把写作的手术刀——精准、锋利,绝不拖泥带水。
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复杂的。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人学的概念也在不断更新。无论如何,只有人更了解人类。
虽然AI是人类发明的,但没有人类的更新创造,AI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AI的写作,从风格到语言,到人物形象塑造,难免会有重复的成分。AI无疑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表现,可以成为人类的助手。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每一位有抱负的作家都力求在每一部作品中展现出不同的自我,塑造独特的风格与内涵。相比之下,AI写作虽能提供技术支持与灵感启发,但在追求深度与个性的文学表达上,仍难以完全满足作家们对创新与超越自我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