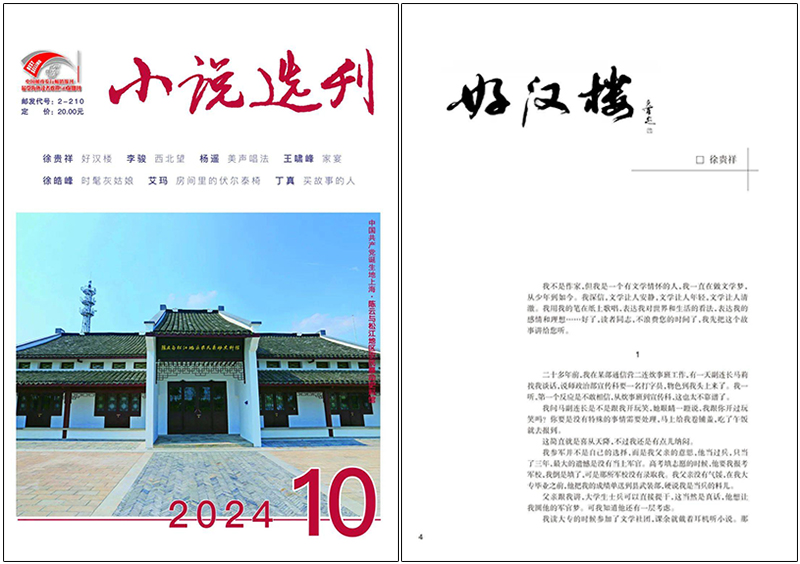
从公文写作到小说创作
——《好汉楼》创作谈
■徐贵祥
1983年,《飞天》杂志第7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几乎与此同时,我由炮兵团“英雄炮兵连”排长调任师政治部群联科干事。
这两件事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调至师机关工作。可是很快我就发现,我似乎并不适合做机关工作。
我所在的野战师,历史上被誉为“猛虎师”。部队作风过硬,机关干部个个精明强干。我所在的政治部,需要撰写大量公文,包括教育大纲、经验总结、典型事迹、动员报告等。
我们科李升成科长个子不高,烟瘾很大。常常,一个重要的任务布置下来之后,便能从科长办公室门缝看到不断飘出的烟雾——那好似是科长浓密的思绪。科长理出思路,便会召集全科人员坐在一起研究。从标题拟定到分段提纲、观点、例证等,都一一推敲。大家贡献智慧,形成初稿,然后再由科长修改。一份公文从酝酿到成文,往往要经过很多道工序,一稿、二稿、三稿甚至五、六稿。
科长的办公桌上,通常放着一盒彩色硬笔。他改稿的时候,目光深邃,思维清晰,手中的笔不断舞动,思想的火花不断闪烁,稿子上彩色的线条和标注符号层层叠加、密密麻麻。科里的干事们也像科长那样,捏着彩笔,如同举着毛刷一遍一遍地洗刷稿件的瑕疵,最终让它成为一篇干净利落、言简意赅、观点新鲜、事例生动、逻辑严谨的高质量文字。
我很快发现,科长和其他干事们似乎都很享受这字斟句酌的乐趣。但我却并不喜欢,甚至有些排斥。只是因为工作,我不得不耐着性子配合。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段经历对我以后当编辑、写小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时的我热衷于写诗,我的脑海里经常跳跃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参与集体研究的时候我常常走神,任凭思绪飞到辽阔的戈壁和雄浑的远山,想象着在那里构建一个独特的空间,让自己的青春在金戈铁马的洪流中燃烧。
1984年春节后,我被借调到集团军政治部,依然需要写公文,而且是要求更高的公文。正课时间,我跟着大家一起认真地工作;业余时间,我经常往市图书馆跑,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那年7月,集团军组建侦察大队,通知机关干部志愿报名。我立即给所在师政治部领导打电话,要求参加。政治部领导大约考虑我曾经有到前线执行重大任务的经历,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
任务来得急,我当即回到师政治部单身宿舍,打点行装。当时,我们政治部秘书科有位管理员,名叫李大海,为人忠厚,低调简朴。他帮助我洗被褥和蚊帐,并帮我准备去前线的一应物资。一年后,我从前线回来,发现当初打算扔掉的一双破凉鞋,竟被他修补好了,变得精美柔软。他拿着这双鞋对我说:“新鞋好看,旧鞋舒服。兄弟,它在等你回来,它终于把你等回来了。”我愣了半晌,终于明白了,这位老兄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对我的关怀。那双凉鞋,我又穿了好几年。
回到科里,科长要我讲讲前线的故事。我简单地讲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很快就喜形于色地告诉大家,我在前线写了6部中篇小说。我津津乐道,讲得忘乎所以。
一位老干事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写小说。你就没想到,有一天你可能会牺牲?
我说,就是因为想到我可能会牺牲,所以我才马不停蹄地写小说,我要赶在那颗子弹抵达我的脑门之前,为我的小说写一个好的结尾。
科长说:“我明白了,在群联科工作,确实不是你的理想。你带兵去吧,好好体验生活,我祝愿你早日当一个作家。我们师历史上就出现过一个作家,也许,你能成为第二个。”
果然,这以后,我就到基层带兵了。几年后,我考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2024年的一次聚会上,我和几名战友聊起我们的年轻时代,讲起我们的“单身宿舍”,和当年凑在一起写作公文的经历,唤起了我的回忆,顿时灵感喷涌。我这才意识到,当年写作公文时对语言文字精雕细琢的态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注入我的血液,成为我日后写作的基本功。我深深感谢那段经历,感谢我的老科长和老同事,也包括李大海和那双旧凉鞋。
一个月后,我写下小说《好汉楼》,致敬我们的青春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