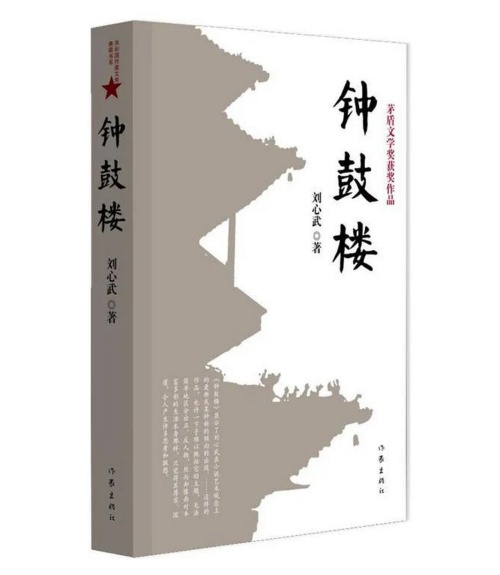
要努力把自己绽圆了
——漫谈长篇小说创作
■刘心武
小说按篇幅一般分为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这个体裁很重要。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热衷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最后在文学史上占有席位。当然,也有的作家一生未写长篇小说,但在文学史上不但占有席位,而且成为文学创作高峰。比如俄罗斯作家安东·契诃夫、我们自己民族的鲁迅。
我是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而且很早就尝试投稿。前几年经常有记者问我:“刘老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处女作《班主任》发表的前后情况?”我只好解释,这不是我的处女作,《班主任》1977年发表,我的处女作1958年就发表了。那年我16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对苏联小说《第四十一》的评论。
2012年我出版了文存,收进了从1958年到2010年我的所有作品。我把《班主任》之前的这些文字收为一本,叫做《懵懂集》。《班主任》之前,我的写作都是懵懵懂懂的,《班主任》是我个人的一次觉醒。
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那次会议上,茅盾先生鼓励中青年作家在写出了优秀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后,要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只发表过短篇小说,开始写中篇小说,还没打算写长篇。会上茅盾先生来了一句——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刘心武来了吗?”我立刻站起来,和茅盾先生四目相对。我们对视的时间只有几秒,但他的眼神给我的滋养非常丰富,既有关心,也有鼓励,还有期望,我感动极了。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写长篇。
写长篇小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写什么?第二是怎么写?首先解决写什么。当时我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思来想去,我要写北京市民生活。因为我熟悉。我1950年8岁时跟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从此就一直定居北京。
当时要求深入生活,需要蹲点。我去了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本是一座寺庙,名为隆福寺,前门在隆福寺街,后门位于钱粮胡同。我少年时代就住在钱粮胡同,上小学和中学都要穿过隆福寺,目睹它从一个寺庙变成了一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门之前,我就和售货员一起去仓库里搬货、补货,然后上柜台售货,商场关门了之后继续盘点、清货,参与了商场营业的全过程,也接触到营业期间在售货员、顾客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跟售货员熟悉之后,我还得寸进尺地提出去人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去他们居住的四合院里,这样我就对胡同、杂院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深入生活的触角越来越多,生活积累越来越丰厚。
题材就这样确定了——北京市民生活。但这只是我要写的内容,并不能算“写什么”这个问题的全部回答。我究竟要通过这部作品探索和表达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象征性的符码——钟鼓楼。

▲作家刘心武近照。
钟鼓楼位于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是两座明代修建的古老建筑,用于报时,具有充分的符码性。我写北京市民生活,而且我要把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写,探讨时间的意义:时间流淌过城市,就形成了历史;时间淌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钟鼓楼》前面有题词:“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我要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
“写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写”。关于“怎么写”,我有一些体会。我认为写小小说要注重情趣,以情趣取胜;短篇小说开始容纳思想,需要有一个好的主题;中篇小说前两点都得有,还要把握整个文本的情调。我揣摩鲁迅的小说,就特别重视他每篇小说所形成的不同的叙述调式,例如《狂人日记》是亢奋、激昂的调式:“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救救孩子!”例如《伤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则是惆怅、哀怨和忏悔的调式。
长篇小说最要紧的是结构问题。中外有很多优秀作品的结构都可以参照。如“串珠式”,把“我”的人生中一些重要的生命片段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有一种我将其称为“登楼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写的:主角在少年时代初尝情感的甜美,这是一个台阶,后来他进入音乐界,与父亲一起去宫廷演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后到了巴黎,进入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场所,谱出伟大的乐章。此外还有“横剖式”等。阅读了大量作品后,我最想学习的是李劼人《死水微澜》的结构,我将其称为“编辫式”,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纠缠、扭结在一起,就好像把三缕头发编成一条美丽的辫子。
但到头来我不想模仿前人的既有结构,我应该在结构上创新。我最后独创了一个结构,我将其称为“橘瓣式”。
在人物设置上,我参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人物,你找不出哪个人物是主角,但你能找到每个片段里的主角。例如船过虹桥那段,船上的船夫就是主角。我将《钟鼓楼》的故事设置在1982年12月12日早上5点到下午5点,空间是钟鼓楼下的普通四合院。这个四合院里有十来户人家,每一户人家就好比一个橘子瓣,具有相对的封闭性,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就像橘子瓣合拢之后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子瓣还需要有橘子皮包裹。橘子皮是什么?就是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把整个四合院的人家都牵连进去,还把院外的人也吸进来了。2021年,美国亚马逊穿越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钟鼓楼》英译本,译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对》。我同意这样的译法。
《钟鼓楼》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在茅盾先生的鼓励下,一直坚持长篇小说的写作,后来又写了《四牌楼》《栖凤楼》,与《钟鼓楼》构成“三楼系列”,还写了《风过耳》,本世纪又推出了《飘窗》《邮轮碎片》。我坚持与时代同步,以小说形式为社会进程留痕,在人性探索、人生意义的追问以及结构创新、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功夫。
多年来,我在文学大观园里始终没有消失,在默默劳作。我在写作上追求美,同时也包容自己,不追求完美。我是小小的、米粒大的苔花,但是我也开放,我要努力把自己绽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