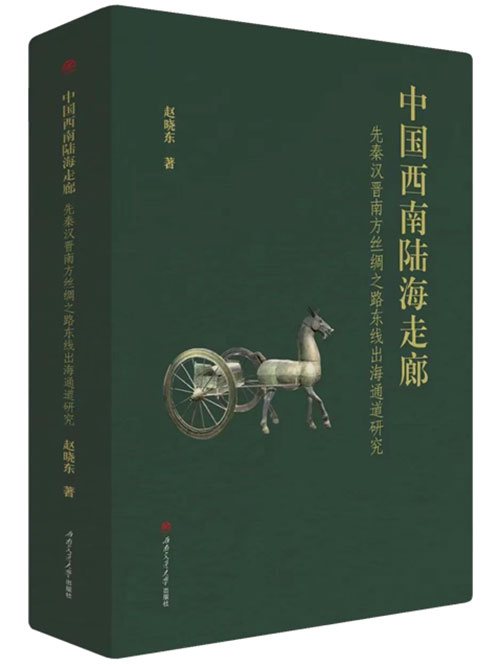
七载呕血著 半部西南史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阅读印记
■军旅作家 王毅
东汉刘熙著《释名》曰:“道,蹈也;路,露也,人所践蹈而露也。”
早在50万年至170万年前,先后生存于中华大地上的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在狩猎、搬运、迁徙等过程中,就有意识去开辟道路,是为最早的交通建设行为。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交通建设往往与经济、政治、军事等紧密相联;同时,交通建设也带动了各地区、各民族物质、文化、文明的融汇与交流、繁荣与进步。
尧舜时期,道路曾被称作“康衢”。西周时期,人们把可通行三辆马车的地方称作“路”,可通行两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道”,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途”。而牛车所行称之为“畛”,仅能走牛、马的乡间小道是为“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兴路政,最宽敞的道路称为“驰道”,即天子驰车之“道”。清朝末年,我国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路,被称作“汽车路”,又称“公路”,其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古代,开辟最早、影响最广、历史最为悠久的路,莫过于丝绸之路。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是时,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起点位于长安,东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起点则位于洛阳。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商旅之路,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人员往来、货物贸易和文化交流。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而后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上述丝绸之路又称“陆上丝绸之路”,与之相对应的“海上丝绸之路”,于世人而言则相对陌生。“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至隋,繁荣于唐、宋、元、明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2019年8月15日,由国家发改委重磅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则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全新升级、雄阔擘画。作为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为加快通道和物流设施建设,提升运输能力和物流发展质量效率,深化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政策支撑和有力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深谙南海丝绸之路之重要性的四川省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晓东先生,早在数年前就将目光放在了南海丝绸之路上,历经七年呕心沥血,最终著成《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以下简称《中国西南陆海走廊》)。86万余文字、近400幅图片、10余幅各类地图……《中国西南陆海走廊》视野之宏阔、历史之厚重、史料之翔实、门类之广泛、笔触之细腻、制书之严谨,远非这三组简短数据所能涵盖囊括,说“七载呕血著,半部西南史”,实不为过。
为深入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东线,赵晓东先生先后20余次往返川滇黔渝桂等省(市、区)实地考察,足迹遍布“走廊”沿线上百座城市,通过系统分析研判,以大量人证物证证实,先秦至汉晋巴蜀通过黔西滇东直到两广和越南中北部,存在一条人际流、物际流、文化流、信息流交通大动脉,既自北向南贯通,亦自南向北发散,其中主要链节点则位于长江、沱江、赤水河交汇的泸州地域。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以十一章主体与结语为骨架,把西南古人类遗迹、古民族生活迁徙、古方国迭变、古城邑布局、古文物分析、古水陆道功用、古军事利用,以及小语种语言分布、古文化孑遗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实地印证,再证诸各类文献,详实推论经泸州、安顺、泸西、剥隘、百色等节点,进入番禺(今广州)、合浦、日南(今越南中部)等南海海域,不仅先秦汉晋时期有网络状道路勾连其间,而且指出学术上应该定义为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同时也是彼时中国西南的出海通道,而之前论证成立的经宜宾、昭通等节点到达缅印的道路,应该改定名为中线。这一全新理念的提出,也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提出了颇有裨益的新的思路和启示。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第一章“巴蜀达南海: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概念提炼”,详细讲述西南段虞夏商梁州、周朝雍州下南海,汉晋益南道繁荣的历史。《尚书·夏书·禹贡》所谓“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指的是青海,《山海经》所谓“南海之内,有衡山”和《尸子》所谓桀纣“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指的才是南中国海。源发梁益,汇点南海,先秦“南冥”指南方溟海,东汉“涨海”以泛潮起名,杨炯《王湛碑》仍为“涨海”,《唐书·地理志》则言:“南海,在海丰县南五十里,即涨海。”赵晓东先生抓住三个三角形节点,重新定义了南方丝绸之路东线。
第二章“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研究缘起及现实意义”,探索了泸州道研究缘起,讲述了大型实地考察过程,梳理了小型考察重点回顾,分析了考察中的思考。第三章“走廊是华夏文化缘巴蜀南延的载体”,阐述巴蜀的“市”是西南经济文化高地,提出巴蜀向南流布文化的考古学证据,解释沱江是蜀中南向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佐证“忠孝文化带”亘古即在沱江“流淌”。第四章“南路文化北上证明陆海互通”,以“从南而来与沿海北进的舶来品”“胡人:舣舟北望的一路佛缘”“铜鼓:南北互动的典型器物”“僚人北迁:铺天盖地的通道利用”四个部分,多角度印证“陆海互通”。第五章“沿线族群互动证明走廊被频繁利用”,又以“沿线古人类活动活跃”“西南拓路先锋:西进南转的百濮群体”“苴侯僰侯:巴蜀地域星星点灯的先秦方国”“沿线小语种族群与走廊通道”,诸方位力证中国西南陆海“天然存在”“被频繁利用”。
第六章至第十一章,分别从“沿线秦汉古县以基点方式支撑通道”“夜郎临牂牁江及右江上游通道价值”“沿线重大军事行动凸显走廊通道关键”“‘盐’‘铁’‘僮’贸易支撑走廊形成特殊通道”“华夏文化认同保障走廊长期稳固”“再说川盐:巴蜀华夏化云贵的长期载体”六个不同角度,全方位、大纵深、多角度研究论证、或考察记述置邑的目的之一为保障通道安全、夜郎国邑中心定位及与滇的关系、通达南越的牂牁江不是红水河及其上游、鳛部道战争是中原文化深入南夷的重要载体、庄蹻“循江”与“王滇”之间的地理距离、争夺“僮盐通道”的西南夷小三国战争、奴隶贸易吸引商贾“持窃出市”、盐铁刚需促使方国大开国门、“故俗”文化共存营造宽政环境、秦争巴盐而一统天下、文化趋同是经济的自然表现等,围绕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主线,合纵上下数千年的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语言等辉煌灿烂历史。
以人为鉴明得失,以史为鉴知兴替。《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作者赵晓东先生不仅以深入细致的考察、翔实权威的资料、科学严谨的推论,娓娓道出西南陆海走廊通道的具体走向、沱江—赤水河是巴蜀南向主通道之一、右江及其上游地域是云贵南出岭南北向的主通道、巴蜀—南海经云贵中转先秦即有文化沿走廊互动、夜郎和滇等西南夷主要方国控制通道、秦汉郡县设置沿走廊形成控制堡垒、民族迁徙和华夏化融合左右走廊全线贯通……还以史学之明、哲学之思、文学之美给人以浸润滋养、浇灌提升。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中国西南陆海走廊》除了从历史方位梳理归纳了中国西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源远流长,还深入探讨了陆海相互联通的战略意义和可能带来的政治经济效益。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发布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推动构建,都为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作用发挥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相信生逢其时的《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一书,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相关部门提供更加翔实的信息支援、更加完备的学术支撑和和更加权威的实践支持。这部不可多得的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巨著,作为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语言等历尽千辛万苦找回的厚重历史记忆,也应该珍视珍藏,并将它交给我们的后代,交给我们的未来,交给我们共生共荣的美好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