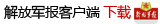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是人们共享与共创的知识资源、文化作品以及生活方式等,“共享”是指借助共同文化,人们进行交往并达成共识;“共创”是指在共同生活与相互学习过程中,人们创造了能够共享的文化。辩证地看,“共享”与“共创”不存在绝对的先后关系,它们共同确立的共同文化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于此,一方面,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文化是共同体确立的基石,是共同体成员团结的纽带,是共同体自我完善的保障;另一方面,他们指出:为了适应风险时代共同体的需求,就必须相应地丰富共同文化的内容。为此,他们另将一些作品确认为交往中介,并重新阐释了一些理论著作,扩展了“共同的创伤性记忆”的内涵。
一、多维的共同文化
对于共同文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出,它并非同一的、强制的,而是多维的、平等的,“多维”是指依据共同体的确立、团结与自我完善等需求,共同文化大致上可分为共享的知识资源、共知的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以及“共同的创伤性记忆”等三个层面;“平等”是指这三个层面在共同体中所担负的责任没有主次之分,最终都是为了人类谋求更多的幸福。
其一,共享的知识资源是人们交往与达成共识的基础。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享的知识资源大致上是指交往者共同使用的语言与共同享有的文化知识。借助它们交往者能够自然地交往,也容易达成共识,这有助于他们解决一般意义上的共同困难。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民族以及全人类拥有着相应的共享资源,如霍耐特指出,借助共享的语言和共创的生活方式,亚文化群体增进了团结,形成了一定政治力量;萨特认为,处于法国殖民中的阿尔及利亚人,在共同学习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构成一种同一的反殖民力量;哈贝马斯肯定道,宗教的某些“世俗的真理内容”有助于人类保持社会与人格的共生。总体上看,借助共享的知识资源,人们增进了身份认同与合作,减少了误解和矛盾,组成了一个团结的共同体。
其二,共知的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既是人们对话的中介与团结的纽带,又提供着“对话”和“团结”等思想资源。在威廉斯等人眼中,共知的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主要是指人们不断阐释与传播的经典作品和著作,如华兹华斯的《华兹华斯诗选》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它们为人们共知并影响着行为和生活。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一方面,这些作品和著作是人们对话的中介与团结的纽带,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种更亲密的志趣交往;另一方面,它们提供着丰厚的“对话”和“团结”等思想资源,增进了人们对 “团结”和“对话”等内涵及其实践方式的认识。围绕这些作品和著作,人们在构建一个文学交流与政治商谈共同体的基础上,更懂得如何增加共同体的团结,有效应对和处理公共事件。
其三,共同的创伤性记忆提醒人们协商和团结的重要性,减少了爆发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将“共同的创伤性记忆”视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当然,这是人们不愿意面对的一种文化或文明的伤疤,它主要充满着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所遗留下的普遍性痛苦,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等。经过诸多思想家的不断反思和阐释,奥斯维辛等事件逐渐沉淀为人们共知的一种消极文化或一桩文明丑闻,它们迫使人们必须面对这种“人为的悲剧”,并在不断反省文化或文明中,采取对话和协商方式去解决猜忌与冲突,从而减少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隐患。为此,鲍曼提醒道,经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人类需要谨记,一旦现代科技被误用,道德悲剧就会恶化为毁灭性的自然悲剧。
二、共同文化的多重角色与共同体建构
历时地看,在共同体建构与自我完善中,共同文化扮演了多重角色:它是共同体确立的基石,是共同体成员团结的纽带,是共同体自我完善的保障。其中,多维的共同文化大致上对应着这些多重角色,如共知的艺术作品和著作的更大价值体现在“共同体成员团结的纽带”中。不过,共时地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多维的共同文化并不绝对一一对应于这些多重角色,因为有时某种共同文化兼顾着多种职责,如共享的知识资源同时担当着共同体的基石与共同体团结的纽带等职能,而这种“兼顾”特性能够将人们紧密团结起来,增强共同体的牢固性,从而为更多人创造平等和民主等契机。
其一,作为共同体确立的基石,人们借助共同文化顺畅地商谈着共同体建构中的诸多事项。在确立共同体时,共同文化在其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例如共享的语言是人们沟通和对话的基础,通过它人们通畅地商谈建构共同体的目的、步骤以及应对困难的方式。再如共知的艺术作品与理论著作扮演着人们交往的纽带,并提供了共同体的相关宗旨。对此威廉斯指出,奥威尔的作品倡导共同体应是一个平等的、共享的场所,韦尔默认为黑格尔的著作论证了完善的伦理生活应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地承认。另外,共同的创伤性记忆从反思的角度明确着共同体的初衷,如欧盟与联合国的宗旨中都凸显着“和平”的重要性,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共同记忆告诫着人们诉诸武力的灾难性后果,也提醒着人们团结的永恒性。
其二,作为共同体成员团结的纽带,共同文化既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又阐释了团结的丰富内涵,还探究了多种团结的途径。例如关于团结的重要性,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在一种共同文化中,人们才能实现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萨特认为,殖民地人们只有实现文化认同,才能结成一种坚定的反抗力量,争取民族独立。而对于团结的内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它涉及亚文化群体的幸福、民族独立以及全人类的安全等方面。至于团结的途径,威廉斯倡导平等尊重每个文化群体,霍耐特提倡公正地承认所有人,并以法律来保证他们的权利。正因为共同文化发挥着这种粘合剂的作用,所以哈贝马斯肯定欧盟之所以能化解许多内部矛盾,保持着欧洲的和平,很大程度上就与各成员国共享欧洲悠久的历史密切相关。
其三,共同文化是共同体自我完善的保障。在为所关怀的对象构建共同体的同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探究着如何完善既有的共同体,以便使它们能为其成员创造出更多的幸福契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共享的知识资源仍是成员沟通和交往的基础,而共知的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则蕴含着取之不竭的共同体思想资源,如通过汲取康德的“宽容”理念,哈贝马斯认为,宽容的共同体能够使更有效地解决公共事件。另外,通过不断地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醒人们协商和团结的重要性,尤其因新的重大事件而出现分歧时,这种共同的创伤性记忆劝告人们对话与商谈的必要性,从而保持着共同体的团结和稳定,继续为人们提供着安全感和温馨感。
三、风险时代的共同体与丰富着的共同文化
随着风险时代的来临,共同体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而为了使共同体更好地履行这些职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适时地丰富着共同体的内涵,如一些作品被确认为交往中介,一些理论著作得以重读,“共同的创伤性记忆”的内涵得到扩展。丰富后的共同文化更有助于共同体解决很多风险问题,从而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受,如安全感和温馨感等。
其一,一些作品被确认为交往中介,它们培养着人们的自由民主等意识,有助于共同体担负更多的责任。风险时代,由于人们同时承受着多重风险以及风险所导致的多重恐惧,因此人们更需要借助共同体来获得安全感,更迫切地要参与到共同体中,为自己以及其他人谋求更多的幸福契机。这就需要更多的、甚至更高级的交往中介,来增进人们的交流与合作。为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确认了一些交往中介,如韦尔默认为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尤利西斯》适合多人一起“立体阅读”,既能培养个人的感知力,又能加强人们的相互学习和交往。同时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既是人们参与和交往的场所,又能培育人们的自由民主等意识,而这既丰富了共同体成员的个人品格,又将共同体完善为能解决更多公共事件的商谈之所。
其二,一些理论著作得到重新阐释,共同体的原则得到了丰富。在风险时代,一些新的棘手问题被凸显出来,例如怎样包容与保护更多难民、如何保证人们有效地履行协议来共同应对风险问题等。为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重读一些理论著作,获得了一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例如通过重读黑格尔耶拿时期的作品,霍耐特收获了承认理论与伦理共同体等相关概念,从而更明确了公正法律在共同体完善中的重要性。哈贝马斯则借助重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指出对于欧盟与联合国这样的共同体而言,一部公正的法律能够更好地督促成员国履行所制定的协议。而哈特与奈格里通过吸收福柯《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的“生命权力”概念,强调共同体应该发挥爱的多重功能,为诸众创造出一个相互关爱和团结的氛围。
其三,“共同的创伤性记忆”内涵得到扩展,使得人们更懂得和平与团结的重要性。风险时代,核威胁和恐怖主义等威胁着人类的安危,而为了建构世界性的共同体与完善既有的共同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思和丰富着“共同的创伤性记忆”,以此不断提醒人们沟通和团结的持久性。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通过继续拷问“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来提醒人们不忘这个痛苦记忆,如鲍曼以“现代性大屠杀”的视角整体地反思现代文明,强调要理性地认识这个“人为悲剧”;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家又以“9·11”事件为个案,既将它逐渐纳入“共同的创伤性记忆”的范围,来探究这个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又由此联系到奥斯维辛事件,整体地审视人类的文明,从而强调了沟通和团结的恒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