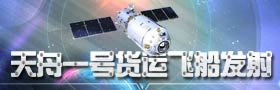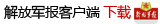当“可能”成为一种主义
●即便能够把“可能”称为一种主义,但它也不能成为一种奢谈空论。“可能”二字,拆开就是:如要可以,必有能力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认为应该依照上一辈的样子过日子,孔子曰“复周礼”,说的就是回归周公《礼记》的要求。而现代社会的人们则认为,比前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要小瞧了这一念之差,它可是工业社会有别于之前其他类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德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将此称为“可能主义”。作为犹太人,赫希曼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诸多传奇,但他的思想比其经历更为引人入胜。他善于在遍地悲观中呼吁乐观,在迷茫和错位间激励获取想象力。他认为人类历史最精彩之处无不证实着“可能主义”——“人永远有以行动改变现实的可能,有从不可能中发现、选择、创造出可能的能力。”
如果感到这话有些拗口,一代伟人毛泽东则把这个道理说得通晓明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星火种遭八方风雨来袭,存之似已不可能;但透过八角楼的那盏灯光,中国共产党人发现、选择、创造出星火燎原的可能和历史。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波兰犹太教师及作家科扎克。从1939年起,这位恂恂儒者一直在所谓犹太隔离区里给孤儿办学,并努力维持着孩子们的正常生活。1942年,纳粹党卫军通知要把孩子们转送去“东方”,科扎克当然知道,其实就是要送去灭绝营和毒气室。上火车时,一个德国军官给了他一份赦免令,可他摇摇头,挥手让德国人离开,然后牵着孩子平静地上了火车。第二天,他和192个孩子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惨遭杀害。
科扎克当然不可能改变这一悲伤的结局,但他却可能和那些年幼的生命一道保持最后的尊严——据目击者回忆,孩子们是举着孤儿学校的绿色旗帜,平静坦然地迎接死亡的;科扎克当然不可能和法西斯讨论身边一百多个孩子的权利,但他却有可能为人类的后代发出呼吁——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就是由他的祖国波兰起草的……
作为作家,科扎克并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但他却用生命的定力、灵魂的纯洁告诉我们,人应当怎样去让被称为“主义”的理想、信念、主张,成为人生的可能。
法国思想家蒙田说过一句话:“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培育自己,不然,到了可能采取行动的时刻,就会不知所措。”即便能够把“可能”称为一种主义,但它也不能成为一种奢谈空论。“可能”二字,拆开就是:如要可以,必有能力。
学界曾有一个著名的10年之赌。1980年,人口生物学家埃利希与经济学家西蒙打赌——铜、镍、锌、锡等几种金属的价格10年后是不是上升。此事的起因是,埃利希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使人类面临资源缺乏的困境;西蒙则认为,科技和商业模式的进步,人类将有可能以超越资源消耗的速度,找到替代稀缺资源的新方案。待到199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10亿,可这几种金属的价格竟全部下降,西蒙赢得了一万美元。与其说是赌一种可能性,倒不如说是学识、眼光、前瞻性等综合素质的比拼。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我很喜欢林语堂的这句诗,因为它提醒人们,人生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自己是有可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