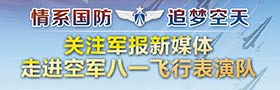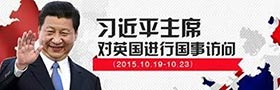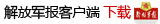上午
战车震撼大地,士兵走向战位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曦光微露中,一个学兵方阵和一个坦克集群巍然列阵。一条弯弯山道泛着清冷的光晕起伏蜿蜒,那就是郭峰的战场——3.75公里坦克专用训练道。
“砰——砰——”两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静寂。第一辆坦克轰鸣着冲向山道。
“我去看看!”话音落处,郭峰已经抵近了进入训练状态的坦克,抵近了他的战位。
观象听音,他调动所有感官搜集着坦克的每个动作、每个动静;观云识雨,他凭借丰富经验判断着每辆坦克可能出现的问题;观剑识器,他用心捕捉着学兵的每个操作细节,为他们成长为一个优秀坦克战斗员而望闻问切……在这3.75公里训练道上,郭峰每天至少要走四五圈,履行着一个教练员的如山职责。
山道一隅,有一个仰角20度左右的土岭。郭峰和一连技术员边志伟守在一旁,瞪大眼睛猫着腰,盯着坦克隆隆开进——换挡,加速,踩油门……坦克又快又稳地“飞”了过去,郭峰高高竖起了大拇指。
边志伟深知,为了这个坡,老郭可没少受伤!按初级驾驶考核大纲要求,土岭挂一挡匀速通过即可过关,但郭峰有自己的看法:技术上这样要求,没错,但未来战场之上岂能离开战术谈技术?“低挡匀速”是技术概念,不是作战概念,选择高挡低挡、低速变速,要因战况而异!
郭峰主张:教学兵开坦克,更要教学兵开着坦克去打仗!
坦克兵都知道,快速翻越土岭,将经受剧烈颠簸,一旦操作不当,极易损毁扭力轴、变速箱,还易导致乘员冲击受伤……
但郭峰决心趟条路出来,他第一个涉险。那段时间,他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散发着红花油的味道。终于,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驾驶坦克高速“飞”过土岭,紧接着一个灵活拐弯,车体隐没在低洼地段……此后,“飞”过土岭成为学兵争相挑战的课目。
像这样的“创新”、类似的“挑战”,郭峰的教学档案里记载着数十个。这条山道说短很短、说长很长,这座训练场说小很小、说大很大——在这里,郭峰不仅把自己淬炼成多型坦克特级、一级驾驶员,成为集驾驶、射击、通信、修理诸专业于一身的“装甲兵王”,还作为“全能教头”,为三军部队培养输送了数千名装甲兵战斗骨干。
“天上,海上,都有从我们基地走出去的学兵!”郭峰的自豪在基地的毕业学兵名录中得到印证:从这里走出的2000多名学兵,汇入了陆军装甲部队的滚滚铁流,跨入了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空降兵从天而降的铁甲战车,其中158人成为特级、一级坦克驾驶员。
基地司令员陈跃告诉记者,这些年,郭峰和战友教技术更教战术,练打靶更练打仗,在全军率先构建起以信息为主导的实战化培训体系。从这3.75公里走出去,可不经适应性训练,直接进入实战。
又一辆坦克越过土岭,尘土四射如礼花。5000多个日夜轮回,这条训练道被坦克履带整整碾下去半米深……
正午
尘土改变不了这个士兵的“颜值”,油污刻画着坦克兵的精神面孔
漫天尘土,尘土漫天,这片训练场上,坦克和士兵都在弥天尘雾中钻入钻出、时隐时现。
要开饭了——钻出尘土的郭峰最后一个来到饭堂。
脸上,像是戴上了一副“灰土面具”,只露一双眼睛、一嘴牙齿。掸掸衣服,像掸一个土口袋,尘土蒸腾。他“嘿嘿”一笑,一双手在门前花坛里抓了把浮土,揉搓,灰黑色的颗粒一坨坨坠落——这双手,像一个未完成的石膏作品,粗粝硌人,不见血管与筋节。
水龙头“哗”的一声吐出雪白的水柱,砸到这双手上,泥点四溅,水池底一道乌黑的水迹。这双手又抓了一把雪白的洗衣粉,揉搓,灰黑色的泡沫一个个泛起,池底一条灰黄的水流。接着,这双手又裹住一块肥皂,里外上下翻转,一个个白里泛黄的泡沫被清水带走……
郭峰这一套复杂而又行云流水的洗手程序,把我们看花了眼。
几道程序下来,郭峰这双手渐渐有了手的模样。但打眼一看,手背、关节、指缝间,依然有顽固的油渍。他边擦手边说:“这些油渍早就渗进去了,洗不掉了……”
这双手,是郭峰和老坦克兵们共有的标识。这双手,粗,硬,看着挺“脏”,抱儿子时,儿子嫌硌得疼……然而在新坦克兵眼里,这种手,是资历,是勋章,甚至是图腾。
12:30,午饭毕。
13:00,另一个学兵队开训,郭峰和战友再次投入训练。
依然是尘土漫天。记者探知,今天算是比较顺利的,郭峰还能吃个热乎饭。如若不然,说不清有多少个中午,因为有维修或其他临时任务,郭峰只能守在训练场,一瓶矿泉水,泡袋方便面,就算是午饭。他的胃就这样吃出了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