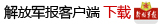核试验场区的营帐
东方巨响
爆炸前的最后一晚,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是在铁塔下度过的。
16日一早,他向基地报告,请求六点开始插接雷管。
插接雷管相当危险,操作中必须保证断电。根据当时九院的规定,插接雷管的人必须带着启爆台上的钥匙,但是基地主控站的规定是不准把钥匙拿出去,根据张蕴钰的回忆,当时,“钥匙”的问题还引发了一场小争执。
最后,张蕴钰自己带着钥匙,随着插接雷管的六名同志,坐着吊篮上到了铁塔上的爆室。
雷管安装完成后,九院的试验部副主任方正合上了起爆机电缆的电闸。
张蕴钰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在上面签了字。
此时,方正合上了最后一道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
那个上午,一道道充满密语的电波在罗布泊与北京之间穿梭: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10点30分,梳完辫子。”“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老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为这颗原子弹长得像一个巨大的“球”。装原子弹的容器代号“梳妆台”,连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电缆线代号“辫子”。
大家都在为最后的时刻忙碌着。
张蕴钰和李觉是最后撤离爆心的,那时距离“零时”还有一个多小时。
回到主控站后,张蕴钰郑重地把钥匙交给在主控室主持试验的张震寰,李觉则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在指挥部等候的、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
当张蕴钰来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的时候,离“零时”已经不到20分钟了。
张蕴钰一直清晰地记着那个时刻,整个罗布泊陷入大战前紧张的静默中。
同是在白云岗,张爱萍将军一直没有按照指令背对爆心卧倒,旁边的人问:“首长怎么不蹲下?”张爱萍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眼睛已经花了,伤一点也没什么。”
老将军就那么一直站着,面朝着铁塔的方向。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韩云升时任基地气象站长,那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他也在白云岗,他后来回忆说,“零时”一过,铁塔处一个像太阳般的大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起,一会儿,一朵蘑菇状的烟云出现在场区中心。
当时,刘西尧急着问他:“你看云顶有多高?”韩云升根据平时的经验回答:至少有7000米。他话还没说完,刘西尧就对着科学家们喊了起来:“7000米以上,7000米以上!”
云顶高度7000米以上,意味着这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
顿时,整个白云岗被欢呼声淹没了。
“零时”之后5分钟,核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通过电话线传到了北京,当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却异常冷静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事实上,原子弹爆炸后十分钟,在马兰基地欢呼的人群之外,防化部队20多个年轻的侦察兵穿着防护服、携带仪器进入了核爆区,他们要在辐射沾染区进行实地侦察作业。
“收回成果和取样队是每一次试验过后第一批进入核污染区的,我自己也进去过很多次。”马国惠说,“这种工作高度危险,要有很好的体力,还要全程穿着密封的防化服,一点都不能马虎。”
正是这些年轻队员的勇敢,换来了第一次核爆后基地最早一批检测数据。
很快,一份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送到基地指挥部,又报到了北京。
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恩来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提前宣布了这一喜讯。
消息一出,举国欢庆。
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当量到底有多大,为了得到最准确的数据,在原子弹爆炸后55分钟,两架伊尔-12运输机从马兰基地旁边的机场腾空而起,飞向爆心点腾起的巨大蘑菇云。
进行核试验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就是分析核装料的裂变燃耗,以此来确定原子弹引爆后是否发生核爆以及核爆的当量。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核爆之后进行飞机取样,获得一定数量的放射性灰尘。虽然技术人员已经对穿云取样的安全程度做过论证,但是放射性灰尘到底对飞行员有什么样的身体危害,大家还是有所疑虑。
明知极其危险,接受飞行任务的郭洪礼机组5名飞行员义无反顾,他们先后穿云三次,收集到足够的样品后,飞机才钻出了蘑菇烟云。
他们取到的样本被送到北京监测分析,几天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确定了我国首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
这一结论,震惊了整个世界。
正如核爆成功第二天周恩来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所说的:“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然而,对于马兰基地上的人们来说,1964年那一声东方的巨响,只是他们在罗布泊荒原奋斗历史辉煌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