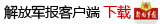小时候,在母亲的臂弯里,我总爱用脸去蹭母亲手腕上那光滑的玉镯。
慢慢,就睡着了,镯子的温润,也洇透了梦。母亲就这样搂着我,听我打着鼾。
镯子啊,轻轻映照出母亲的慈颜。每每想到母亲镯子,暖暖的心里,妥帖而安详。
母亲年轻时,最爱戴手镯。
传统的她对镯子有一份独有的情结。她嫁给父亲时,最珍视的嫁妆就是一双手镯。可是,母亲又怕戴镯子。
在我儿时,母亲喂鸡忘给鸡窝关门,最厉害的一只公鸡窜出来,跳起朝我鼻尖猛叨了一口。
望着我鼻尖涌出的血,母亲深深自责,不住地追着鸡打。哐啷一个响声,在母亲抄家伙拍鸡时,右手镯子坠地了。母亲忍不住跌脚疼惜。但顾不上镯子的事了,母亲赶紧抱着我,在寒风中去村口的中医那里涂药。
一个镯子,是一生绕不过的岁月。

后来,母亲索性摘掉了左手手腕的镯子,母亲那是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