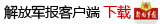在我心里,年有味道,也有温度,是一个甜美又温暖的意象。
小时候对年翘首以盼,还源于奶奶口中的那抹神秘。
过节宜什么忌什么,她会郑重地数如家珍——是为了家人康乐,为娃们讨个好彩头。奶奶在鞭炮声中,在藤椅上,眉飞色舞地讲神话故事。然而,她总跑题。瞧,咂摸着两瓣嘴,不觉就唠叨起她儿时家里的情状。奶奶家是地主,家中文人又多,年俨然成了趣味横生的节庆。许是她从小在年味弥漫中过来,因此她格外希望我也能体验那种密集的欢喜。
怎样可算年味儿十足呢?
儿时给奶奶汇报功课,就显得别有风味。
奶奶每次都逼着我们孩子背诗,我意外来了一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咏诵的塞外诗,让奶奶的眸子里突然烁起清光。
孩子,喜欢军旅的塞外诗吗?
我挠挠头,爱背诗算不算喜爱呢?
那时,从军的种子洒在心里,渐渐破土。

年是很华丽的,能调动所有的味蕾和触感。
年夜饭是奶奶亲自操办,冷拼热炒,清炖细煎,甜食果品,粉蒸嫩烤,她就在案板边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像变戏法一样,色色齐全。
我最爱吃奶奶的黏豆包,还是黄米面的。过年真好,家乡过年也炸麻叶,老年人喜欢用糖水泡着吃,孩子们则是生吞活咽。
那时,嘴巴香香,肚里饱饱,心里暖暖。